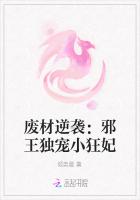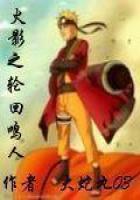小引
年过花甲后,父亲开始记日记。父亲的日记是回忆式的,回忆自己这些年的生活经历及相应的心理感受。因此与其说是日记,倒不如称为回忆录更为合适。然而父亲坚持每日必记,从这个角度讲,称为日记也是可以的。父亲记日记的目的有二,一自然是排遣时日,不使光阴虚度,二来可提供一些素材给我。说来父亲真是用心良苦。父亲陆续记日记已有两年,装订有九册之多。父亲曾当过村里的民办教师,于是就买教师常用的教案本记日记,这种本子一册一元,纸质不是很好,但是父亲说,正适合于他记日记。
父亲的日记我是常常看的,回忆性的文字外,自然不免也还记录一些当下的事情。其实父亲只上过半年学,就因爷爷的劳改而辍学了。父亲的一点文化全是靠自学积累起来的。我觉得读父亲的日记,对我的文风或许也有一些影响的,那就是要实诚、实在、言之有物,不要太多修饰。这也正切合于如今我对文字的要求,就是要丑笨,不要漂亮。但愿这一对文字的要求能始终如此。
我打算把父亲日记中的人事依我所愿,摘录一些下来,如果父亲的日记能坚持写下去,那么这就是一个长期劳动。从今天开始,我就开始我的这个劳动。
陈太太
父亲的日记中很多地方都记到了我的爷爷,爷爷给我们一家的影响实在是太深了。
爷爷是一个喜欢单干、喜欢做生意的人。与人交往主张吃亏、忍让、忠诚、讲义气,因此有不少生活上生意上的朋友。他结拜有八大弟兄,这个后面我也许还要写到吧。刚解放时,村里搞互助组啊、初级社高级社啊等等,时过境迁,可以讲实话了,实话说,爷爷对这些都兴趣不大。爷爷农民出身,却不喜欢种地,喜欢做生意。从父亲的日记里看,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全国都在轰轰烈烈搞大跃进吃大锅饭的时候,爷爷竟还带着十岁左右的父亲,到兰州、上海做生意。主要是贩卖布匹等。据父亲讲,一条裤子的布可以换一口袋粮食,那裤子还没有腰。那时候的裤子,裤子和腰是分开做的。可见布匹在我们这个地方的珍贵。要是在兰州做生意,爷爷他们大多是住在朋友家里。爷爷的朋友真多,父亲列举了他和爷爷几年间住过的地方,有七八家之多。这样可以省一笔开销。而且爷爷如果不住朋友家里,去住旅社,朋友们也会因此不高兴的。父亲说,在兰州的大部分时间,他们是住在华林坪陈占海老人家里。父亲的日记里称陈占海老人为陈爷,称他的女人为陈太太。父亲说,有一次他们在陈爷家一住就是三个月。陈爷家的住房并不是很宽余,老实说,也就一大间房子,吃住都在其中。一个大院子,里面住了十来户人,回汉均有,还有一户藏族。十几家人同进一个大门。大门晚上十点半之前就关了,过了这个时间晚归叫门,门是不大会开的。总之大家都遵守着这样的约定,有事无事,十点半之前都尽可能赶回来。父亲那时候是很不安分的。晚上习惯于到文化宫一带看戏,看大人们跳舞,这样回来就晚了,大门肯定是进不来的。然而不要紧,陈爷的房子正好临街,临街的后窗正好开着一扇小木窗。陈爷鼓励父亲去看热闹。若是晚归,不要高喊,只需轻轻敲三下窗棂即可。陈爷就会打开木窗,把父亲从街上接进屋里来。父亲说那时候木板炕上睡三个人,陈爷、陈太太,另一个就是父亲。爷爷睡在门侧。陈爷在门侧给爷爷支了一张单人床,夜里睡觉用,白天可以取下来靠墙立着,这样就不占地方。我就感慨那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是融洽,相互间能信任到这个程度。
那么陈爷和我家是什么关系呢?陈爷原本也是我们海原人,解放前去靖远开车马店多年,经营有方,挣了不少钱。解放后就搬去兰州了,还在公交公司谋到一份工作。有一年陈爷的女人陈太太生孩子,那时候陈太太快要四十岁了,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孩子这么迟。陈爷很是小心,到处打听接生婆,就辗转打听到爷爷的母亲。我的太太是接生不错。陈爷就派出一个人来把我太太用骡子驮去了。生下一个儿子来,取名陈让。母子平安。陈太太就把我太太认作了干妈。两家之间,也就这么点关系。父亲的日记里,对陈让一家记之甚详。尤其陈太太,看来是给父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父亲的日记里看,这个陈太太,派头很大。喜欢听戏,听说解放前她定期请戏班子来她的店里演戏。她还吸食鸦片。没有鸦片的时候,陈太太看起来就像换了一个人,张嘴打哈欠,脾气也不好了。父亲说总体上讲陈太太的脾气是很好的,善良、宽厚,有些虚荣和幼稚,一看就是大户人家出身。他们虽然只住着一间房子,而且十几家共用一院,这也只是他们的一个策略。实际上他们的老底还是不错的,从陈太太的过日子不慌张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来。再说要是日子不宽余,陈太太是不敢吸食鸦片的。父亲说上世纪六十年代,鸦片也还是很贵的。父亲的日记里也还写到那个陈让。半个世纪过去了,不仅日记里,就是口头上,父亲也多次讲到这个陈让,倒使这个我们不曾见过的陈让,似乎是很熟悉的一个人。父亲说他和爷爷住在陈爷家的时候,陈让已经结婚成家,搬出去住了。小两口有一个孩子,四五岁的样子,已经是不低的个头了。这主要是陈让两口子都是高个头。陈爷陈太太个头也不低的。按说小孙子该常来爷爷奶奶家的,但是陈让一家并不多来陈爷家。陈太太对儿媳有些微词。偶尔陈让一家来了,很少见到婆媳俩说什么。倒是陈爷有一句没一句的和儿媳说一些话。陈太太则是躺在一边抽她的鸦片。或者是逗孙子玩,把什么好吃的拿出来偷偷地给孙子吃,倒似乎不情愿给儿子儿媳看到她的疼孙子。陈太太之所以敢在儿媳面前抽鸦片,一来是她的性格如此,她的性格里有一种我行我素的特点,不在乎人的看法和眼色的;另一个原因是,亲家母也是一个大烟鬼,陈太太说起亲家母,总是要笑话她一顿,说她要是没有大烟抽时,简直连一口气也维持不住了,看上去马上就要油枯灯灭。陈太太的意思是亲家母是个软浆人,她陈太太再怎么没鸦片吸,不过是心里难受,多打几个哈欠而已。而且即使她心里难受,面子上也尽量克制着不表现出来。总之因为对儿媳不满意,陈太太连带着对亲家母也有些轻蔑的。我不说她,我没工夫说她,有说她的工夫我还不如美美睡一觉呢。陈太太一说到亲家母,笑话了她有气无力的软浆后,就会这样提醒自己。果然接下来关于亲家母的好话瞎话,是一句也没有了。父亲说陈让是他见过的世上最洋气的人,高个子,白净面孔,戴着眼镜。父亲对他的评价是,一看就是个知识分子,话很少,一句无用的话都不肯多说。爷爷托陈让办过一些事,陈让都给办了,然而却是由陈爷转告给爷爷。陈让办成事情,从来没有一次直接通知给爷爷。父亲说爷爷认为,这只是因为陈让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缘故。要是别人,事没办或办不成,先给你说上一大堆。父亲关于陈爷家的日记,更多的笔墨是关于陈太太的。陈太太不但是会给自己的小孙子一些好吃的,偶尔也会给父亲一些好吃的,毕竟父亲也是一个孩子嘛。父亲说即使解放后到了六十年代初,陈太太养成的生活习惯也没有改变多少。改不了。她很看重自己的身体,有一个女大夫,每周都来给她查身体两次。作为家里的女主人,她几乎从来不上锅做饭,家里的吃喝都是陈爷一手准备着。连倒尿盆都是陈爷的事。然而陈爷看来是心甘情愿地做着这些。因此别人看来,这一家的生活虽然和别家有不同,但还是很自在的。父亲说陈太太那样的人,让她进皇宫给皇上当妈当女人都可以,都不会有问题。地位越高,派头越大,看来陈太太会越适应。但是让她去农村当个婆姨就不合适。她自己难受,别人看着也觉得把她是搁错了位置。
但是日记的末尾,父亲却写到这样一件事。说是一九六八年,陈爷一家倒霉了。就是那间小屋子,也不让他们住了,把他们赶到火车路去,随便给安排了一个住处罢了。老两口年过古稀的人了,分派给他们的工作是打石子儿。听说陈太太很快就无常了,剩下陈爷一个人继续打石子儿。关于他们的儿子陈让一家,父亲的日记里没有再涉及。我问父亲,父亲说,六三年,爷爷被抓,判刑劳改十年,就再没有和陈家联系过。还联系个啥呢,父亲说陈爷现在肯定是不在了,就是那个给了父亲好印象的陈让,即使健在,也已经快八十岁了。
小朋友
在兰州时,爷爷和父亲还在牛爷家住过。父亲的日记里明白无误地写着,牛爷家当时是在桥门巷12号。牛爷的女人,父亲称呼她为牛奶奶。牛奶奶个头不高,略胖,很能干,家里大小的事情都是她做主张。牛爷尊称她为“我的女掌柜”。牛奶奶如此能干,牛爷乐得凡事甩手不管,只是让牛奶奶把他的吃喝操心好就是了。实际上这不用牛爷说。常常牛爷早晨刚睁开眼睛,牛奶奶给他的馒头就已经蒸好了,奶茶在火炉上正呼呼地冒着热气。牛爷把吃是看重的,在吃嘴上是不亏待自己。然而穿却是不在乎的。牛爷在奶牛厂上班,老实说,也穿不干净个衣服。他常年是一套劳动布衣服,洗不洗好像都是那样子。牛爷说,要是不怕羞丑,我光着身子走都没问题。牛奶奶自己却是收拾得很干净。做活计时总不忘外面罩一件蓝布长衫,这样做完活计,脱去外面的长衫时,她便可以衣着齐整地上街去买菜什么的。这么两个人成为夫妻,平平安安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还生有一大帮儿女,真是不可思议。细细想来真是让人忍俊不禁哪。
牛爷老两口和一个儿媳妇住在一处。这个儿媳妇,人高马大,性格爽直。老两口小两口之间,处得不错。牛奶奶的儿子在白银工作,一周才能回家一次。小两口有一个女儿,文静秀气,身子好像有些虚弱,当时已经是一个小学生了。牛爷牛奶奶很是疼爱这个小孙女儿。据说她小的时候,牛爷没少拿厂里的牛奶喂她。当然只能是偷偷地从厂里拿出牛奶来喂她。一次一小瓶,哪里都装得下的。然而她并没有吃得身体好起来。牛爷笑着说,偷下的牛奶嘛,当然是吃不胖。牛爷一家,是兰州本地人。我们两家相隔近千里,而且一方是城市人,一方来自农村,是怎么牵连上的呢?这都是因为,虽然两家相距甚远,背景不同,但却共同信仰着一个宗派,而且都是伊斯兰教嘎德忍耶门宦的教民,这样,异地相逢,就会很感亲近,一来二去,就成亲戚朋友了。父亲说牛爷牛奶奶虽是城里人,教门上却是极虔谨,六十年代初期,教门方面的政策还不是很严峻,牛奶奶常去小西湖拱北点香的。直到现在也是如此。即使是陌生人,操着不同的方言,有着不同的地位,但只要信仰着同一教派,追随着共同的道祖,互相间很快就会消除戒备,亲和起来。我有时候倒觉得宗教是一种感情或暗号,把人们深切地联络并沟通着。仅只是同一教派的原因,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三十年间,我家从爷爷开始,直到父亲、叔叔,两代人不知多少次打扰过兰州的牛爷牛奶奶。牛爷牛奶奶现已俱成故人,父亲只要说起他们,总是欷歔不已。父亲说八十年代初,他去兰州做小生意,住在牛爷家,每天天不亮,牛奶奶就会呼他和牛爷起来吃馒头喝茶。牛爷喜欢喝奶茶。父亲原本喝不惯奶茶的,后来对奶茶反而是颇有兴味,正是在牛奶奶家喝出习惯的缘故。父亲常说牛奶奶的馒头蒸得有多好啊、牛奶奶收拾得有多干散啊等等,看起来真是情深意重,没齿难忘。但是关于他自己的小朋友的事,父亲从没有给我们讲过,我是不久前才从父亲的日记里看到,原来父亲曾经有过一个小朋友的。就是牛奶奶的那个孙女儿。
父亲那时候也就十一二岁,从日记里看,父亲对那个小女孩的印象是很深的。她好像并不嫌弃父亲是从小地方来的,从乡下来的,对父亲有好感,父亲在日记里记到她给父亲让座啊等等。六十年代初,中国人的日子是很苦的,即使城市人,吃得也并不怎么样。父亲说,不少城市人常常在工作之余,在星期天,成群结队地去城外的田地里寻找吃食,引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认为城市人保障供应还不得够,在农民碗里抢食吃。总之当时中国人的生存条件是极恶劣的,饿死人的事时有发生。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父亲的日记里清楚地写到,那个小女孩还偷偷地给过父亲大豆、干洋芋片等,也不知她是从哪里弄来的。那时候爷爷几乎是铤而走险,依然带着父亲,不时去一趟上海等地跑生意。父亲记得清楚,他们要去上海时,牛奶奶的那个人高马大的儿媳妇就会开玩笑一样对父亲说,让他到上海不要忘了,记着要给自己的媳妇子买上个发卡。她是用兰州话说的,呼着父亲的小名。父亲的日记里也是引用了她的兰州话。所谓媳妇子,指的就是她那个文弱的女儿。父亲那时候还不很理解媳妇子是个什么意思。然而父亲却是把那女人的话记在心里,到上海后,在城隍庙一带给她的女儿买了两个不同样式的发卡,回来交给牛奶奶的儿媳妇。父亲说他一共给那个小姑娘买过两次发卡,一次不多不少,也只是买两个发卡。这样一来,那个小姑娘就开始躲着父亲了,不再像先前那样和父亲亲近了,看见父亲走过来,她会有些慌乱,甚至有些恼怒父亲的意思。但是她也还偷偷送一些吃食给父亲。父亲夜里拉开被子要睡时,被子里就会带出一个小袋子来,里面装着大豆、干洋芋片、干薯片一类。到六二年下半年,风声开始紧起来,地方上派出专人抓爷爷,这样爷爷觉得再带着父亲就有些不很方便了,于是打发父亲回老家来。离开牛奶奶家的时候,那个小女孩知道了消息,在爷爷和父亲后面默默地跟踪了很久。她背着书包,装作是去上学,然而她并没有去上学,她的学校在另一个方向,这一点父亲自然是很清楚的。父亲在日记里疑问道,难道那天她逃学了么?她固执地跟着,就是要送一程父亲。父亲现在回想这件事,想不通,她一个城里女孩子,到底是看上了他的什么。时过半个世纪,父亲在日记里独自回望这件事时,依然心绪难平,在回忆小女孩默默跟在后面的情景时,父亲禁不住有些动情,这样写道:她是希望我不要走啊,希望我还能留下来,再留上一段日子,可是我就走掉了,心里头倒像是没有对她的牵挂,只是牢牢记着她背着书包,跟着我们,走过了几条街的样子……
其实父亲一直记着这个小女孩,父亲称她是自己的“小朋友”。八九十年代,政策渐渐宽松起来,父亲又开始做小生意,每去牛奶奶家,父亲都会想起他的这个小朋友。然而真是奇怪,竟然是一次也没有碰到过。父亲虽是情怀热烈,却是性格内向,不便向牛奶奶打听“小朋友”的下落。只是听说,她是嫁到天水去了,有三个孩子,丈夫是很能干的一个人。
父亲在他的日记里总结说:这些年去过牛爷家多次,没见过她,细细想,这是最好的,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再没有比相互之间不见面更合适更圆满的了。
爷爷
爷爷在上海,前后被捉获过六次,五次都侥幸逃脱了。爷爷名叫田义福,被捕获的时候,审讯记录上,爷爷的名字叫杨生明。那时候和爷爷一同到上海做生意的本地人,有七八人之多。大家无一用的是真名实姓。我父亲当时不过十岁左右,然而也不敢用真名实姓。爷爷的一个好朋友叫鲍玉财,介绍信上他叫鲍风良,父亲充作他的侄子,叫鲍布拉。父亲的经名叫布拉,于是就叫了这么个名字。父亲说,那时候有些人不敢用自己的真实姓名,这是很难受的一件事,你要时时记着自己的假名字,别人呼你的时候,你不能有迟疑,要立即有反应。父亲说尤其爷爷有时候也喊他鲍布拉时,使他有很古怪的感觉。其实这些人,做的都是正规生意,而且无不是小本生意。只是时代不允准如此,于是原本再正常不过的事就变得复杂且异样了。父亲说,假若一个时代不允许人们用嘴说话,只可用眼神交流,只可打手势,那么开口说话就会成为让人骇惧的事情。众目睽睽之下,轻易开口说话的人就会被人看成怪物,看成犯罪者,判什么刑都是可以的。政府的法令会默化成一种公众意识。甚至像爷爷他们这些做小生意的人,因不能光明正大地来做,因偷偷摸摸地做着,就总是不免有负罪感,不慎让给逮住了,也是没有怨言,束手就擒便是。譬如爷爷因买卖几丈白布给判了极刑,在那样的时代里,爷爷自己也会认罪伏法的吧。父亲说,要是现在,做着这么点可怜的小生意还要惊恐莫名,更名换姓,一定是连疯子也会觉得不理解了。
父亲在日记里放任地议论说,对老百姓来讲,认罪伏法其实是很容易的。譬如有皇帝的时候,一个老百姓要是运气不好,碰上了帝王将相列队出行,使人家的车马受惊,那便大祸临头了,判他一个满门抄斩,他也会只怪自己命运不好,自认倒霉罢了,不会埋怨到别处的。只要公家列出条条款款,老百姓立刻就会张口结舌,认罪伏法的。
然而老百姓也自有其狡黠、灵便的一面,要是给公家捉获了,实在动弹不得,那就认罪受法,一旦有机会逃跑,那也不失时机,即可逃逸。因此像爷爷那样表面上显得愚讷的人,也有着其六擒五逃的经历。这是我最佩服爷爷的地方。
在父亲的日记里,有一则日记篇幅较长,而且父亲还给加了标题,叫“难忘的夜晚”,记的正是爷爷在上海第一次遭擒,又成功脱逃的事。
那天夜里有些热闹。在爷爷租住的旅社里,聚齐了在上海做生意的老乡,其中就有在逃犯李得桂老人。这个老人我后面还要写到。大家正谈得热闹,父亲下楼去拿信件,忽然看到两个便衣,正在和旅社的经理鬼祟地说着什么。父亲当时虽不过十岁左右,然而已能察觉一些事情了,立即跑上来报告了情况。热闹中的人们立刻安静了下来。但还来不及议论,两个便衣已推门进来,查证件问来历。问到谁谁回答。都没答出什么破绽来。尤其是李得桂老人,镇定应对,谈笑自若,哪里像个被判刑十八年的在逃犯。还有他的两个儿子,在他们父亲的镇静里定下心来,应付得滴水不漏。父亲睡在一张小床上,欠起身来要配合检查,但是便衣按着他的胳膊不让他起来,说小孩子不检查。父亲主动说我叫鲍布拉。没有人理他。没有查出什么来。两个便衣训话说,要提高警惕,防备坏人坏事,最近上海抓得很紧。说了这些便衣就走掉了。其实这是便衣的一个计谋。他们先来看看动向,然后再做行动。夜里十二点的时候,那两个便衣又带着几个人来,不容分说让爷爷和李得桂老人从床上起来。那时候其他人都已走掉了,原本李得桂老人也要走,爷爷把他留下来说话,他也就留了下来。他们两个顺从地起来。便衣让他们跟着走一趟。好在并没有上铐子。父亲惊醒来,望着这一切。爷爷临走时装作过来给父亲说什么,顺手把一个装钱的小包塞进父亲的被子里,同时示意父亲去找叔叔鲍玉财。这样爷爷和李得桂老人就给带走了。旅社的房间里只剩下父亲一个人。父亲立即撕去裤裆里的一些棉花,把爷爷留给他的四百多块钱装进去。还是不放心,凌晨两点左右,父亲装作出门方便,想把钱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不仅钱,父亲身上也还有一些空白证明。只有公章而无文字,根据需要自行填写便是。这些空白证明,都是当时队里的会计田文福偷开给爷爷的。父亲推门出来,几乎跌了一跤。就看到原来是旅社里的一个人,蜷缩着身子睡在门口。那是个讨厌的人,绰号“瘦猴”。瘦猴抬头一看是父亲,当知道他是要去撒尿,就倒在门口又睡了。
父亲跑上楼顶,把钱和证明藏好,这才下去睡觉。一觉睡到第二天快中午了,被鲍玉财喊起来。这个鲍玉财,和爷爷可以说是生死之交。当即就骂了父亲一顿,说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大睡。让父亲赶紧收拾东西跟他走。父亲于是上楼去拿东西。等他下来时鲍玉财已不见了。他们还约有见面的地方的。到那里,果然看见鲍玉财在那里慌张地等着,看到父亲,拉下帽檐转身就走。父亲顺从地跟在后面。原来刚才鲍玉财在父亲的房里等着时,忽听声音不对,忙出门看,见走廊两边,各有一人,面色阴沉地向房子逼来。鲍玉财慌不择路,跳下二楼跑掉了。鲍玉财领着父亲,走到南京路沈阳路交会处,大吃一惊,他们看见一个人笑呵呵的向他们走来。那不是别人,正是爷爷。简直叫人不敢相信。原来昨夜便衣带着爷爷和李得桂老人在街上走时,爷爷突然一瘸一拐,显得行动不便起来。但还是勉强能走。要是装作完全不能走,便衣就会想办法了。爷爷的介绍信写的什么?写的就是爷爷腿有病疾,来上海不为别事,正是来看这个病的,因此爷爷就一瘸一拐地走着,李得桂老人也在一边帮着说话,让爷爷缓步慢行,一边还给便衣解释着,求得谅解。走了一段,爷爷提出要小便,申请了几次,终于给同意了。爷爷装作向暗处去,后面跟紧着一个便衣。但是爷爷忽然就跑起来,听到后面一片喊捉拿声。路人纷纷侧头看着。爷爷也扬臂高喊着捉住捉住,好像被捉的人正在前面。就在这慌乱中爷爷逃脱了。再不敢去旅社,任何一家旅社也不敢去住了。爷爷有一个姓葛的汉族朋友,爷爷到他家住了一晚上。想着要是不出意外,鲍玉财带着父亲一定路过这里呢。没想到真的给碰上了。三个人高兴得很。父亲说到夜里出门时,门口睡着瘦猴。爷爷庆幸不已,说果然是没有回旅社去,不然正好是送到了人家的手里。一定是看守所给旅社下了命令,旅社才派瘦猴守株待兔。爷爷他们对那个旅社的经理很是小看了,决定以后不再住他那里。我看着父亲的这些日记,真是觉得难以置信。他们不过是几个做小买卖的人,竟搞得如此神鬼莫测,兴师动众。即使真的用大炮打蚊子,也没有这样滑稽。但是爷爷他们,包括十岁左右的父亲,当时却是半点滑稽之感也没的吧。
爷爷被擒六次,脱逃五次,然而父亲只是详尽记录了这一次脱逃的经历,其余五次,均无详细记述,其实我是很想知道的。爷爷并非武林高手,实在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他是靠什么一次次脱逃的呢?既已逃脱,为什么不一径逃出上海,而最终被擒于上海呢?关于爷爷的被抓难逃的那次,父亲的日记虽只寥寥记录了几笔,却还是能看出大概的。一天,爷爷、鲍玉财还有父亲三人上街,边边有耍猴卖艺的。父亲就拖了鲍玉财去看。爷爷也在另一端看着的。但是忽然间看客们骚动起来。父亲和鲍玉财眼睁睁地看到两个便衣,一边一个扭了爷爷的胳膊,钻进一辆车里,一瞬间就不见了。
这一次再没有听到爷爷成功脱逃的消息。
不久我县的公安就赴上海将爷爷押回原籍,判刑十年。鲍玉财也给捉住了,他因为脾气大,和逮他的公安打架,获刑二十年。
直到爷爷被判刑去劳改后,家里才知道这些年来爷爷并没有挣到多少钱。
爷爷去劳改后,我家的生活迅疾困顿下来。那是六三年的时候,家里的锅灶到吃饭的时候也冰凉着,没法子热火起来了。
讨债
爷爷在劳改队来了信,列出一个清单来,让父亲去找清单上的人讨债,好度过那一段艰难的日子。
爷爷去劳改时,我家里非老即少,最年长者是爷爷的奶奶,快一百岁了。接下来是爷爷的母亲,还有我奶奶。我奶奶当时三十七岁。然后是父亲兄弟姐妹五人,父亲最大,当时十三岁,最小的叔叔,爷爷劳改有半年时才生下来。说来当时家里的壮劳力只有我奶奶。然而叔叔只一岁稍过,奶奶就去世了。就在奶奶去世那年,一九六三年,我家的几个老人就像商量好了似的,一一离开了人世,把生活的担子都压在了当时只有十四岁的父亲身上,父亲的日记里有不少篇幅记的都是那些年他是怎么带着弟弟妹妹们过来的。
好在我们还有些账债可以讨要。依爷爷的秉性,不到万不得已,哪里会做出上门讨债的事来。上门和朋友们催讨过欠债,这是爷爷一辈子的心病。父亲说,爷爷这是为了家里那几个还没成年的娃娃,要为他自己,他是绝不会给他的朋友们来这一手的。
父亲拿着爷爷列出的单子去讨债。
第一站是去甘肃靖远。九十多公里路,徒步去。父亲虽也见过大世面,毕竟一直是跟着爷爷的,有依靠,此番却是一个人出门在外,而且还是去讨债,不是什么光彩、容易的事。父亲一路上边走边想,边走边哭。关于讨债的经历,父亲也写了不少。有两件事看来给父亲感慨很深。靖远西关有一个老银匠,是一个汉族老人,姓文,叫文长生,父亲叫他文阿爷,有爷爷一些钱,不多。父亲先是去了他家,阿爷阿爷的叫着,说了困难。文阿爷也很难过,说你大这个人我是知道的,他在劳改队上没办法出来才开这个口呢,不然他不会开这个口的。文阿爷给了父亲八对手镯,一些手箍、耳坠,算清了爷爷和他之间的账债。文阿爷还把父亲带去街上的饭馆里吃了一顿。叮嘱父亲说,再去谁家要账,记住,先不要说你大劳改的话,就说老人手头紧,派着要账来了。文阿爷这样的叮嘱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并不是每个人都是文阿爷,都能体会到爷爷的不得已。父亲去南门的老妥家讨债时,就遇到了麻烦。当时父亲到老妥家里去,一屋子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坐在那里和面捏饺子。老妥也在其中。因老妥一家是回民,父亲就以回族的礼节给他们躬身道色俩目。然而他们却哄笑起来,尤其一个年轻的长相还不错的小媳妇,竟至于笑得捏不成饺子,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这有什么好笑的呢?道个色俩目,有什么好笑的呢?穆斯林之间,不就是看重个互道色俩目么?妥家人的一哄而笑让父亲既尴尬又不解,还有些愤怒。真是,道个色俩目,至于笑到这个样子?妥家捏的是黑面饺子,照这样说,你一个年轻媳妇捏黑面饺子,不也是好笑的么?那实在比道色俩目还要好笑,我不顾体统地笑上一场可以么?总之这个不合时宜莫名其妙的笑让父亲记忆深刻,成见颇大,只想快快讨了债离开这里。妥老汉毕竟是个老汉了嘛,他还是掩饰着笑意接了父亲的色俩目。但是听清父亲的来意后,他却要爷爷亲自来算账。说父亲一个碎娃娃,说不清道不明。原来父亲照文阿爷的叮嘱,没说出爷爷劳改受法的事。见老妥这样说,父亲只好把隐瞒的事说出来。老妥不高兴地说,你看你还给我扯谎,其实我早就知道你大的事呢。父亲的隐瞒不说似乎让老妥很生气,他坚持等爷爷回来再还债。父亲又拿出爷爷的信给他看。他很认真地看着,像在辨识真伪。但还是说,尕娃,不要着急,账肯定是要还呢,等你大回来再说吧。
就是这么个结果。
他们留父亲吃他们的黑面饺子,但是父亲愤然出来了。父亲心说,不要说你的黑面饺子,你就是把白面饺子做上端上来,我也不稀罕了。
没想到这件事给父亲的印象如此深,触动那么大,父亲在他的日记里就此发了很多的感慨,感慨的篇幅大过了对这件事的记录。
父亲说,从那时起,只要是眼神不干净,表情不庄重的人,即使是长辈,对不起,他也不会给说色俩目了。
父亲很后悔把文阿爷的那些银饰拿回来就变卖成钱。文阿爷是靖远一带有名的银匠,他的手镯、耳坠,留到今天,一定是能卖个好价钱的。当时的一对银镯才卖三块钱,真是白送给人了。
我知道父亲这样说的时候,也只是说说而已,心里一定是别有主张的。也许这不过是他惦念、欣赏文阿爷的一种方式吧。
写于2009年6月三岔河
刊于《人民文学》200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