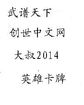肥皂泡一样的泡影,有大有小,大的像小型的星球,小的可以放在掌心里。
林晋仰头去看,一幕幕光影在泡影上闪现过去:离群索居的上班生活,在凋敝的出租屋里,用廉价手机录下日常生活的场景,以及,荒凉的院子和相继离世的二老。
作为孤儿的他,世上唯一的亲人就是他们。原想等赚得足够多的钱后,好好报答一番,但时间不等人,如今那两堆土坯上应该生满荒草了吧。
两个善良的老人,十八年如一日地把全部精力倾注在他身上。即便到了今天,他也常常感到不可思议,他们因何这么疼爱一个性情乖僻且无血缘关系的孤儿呢?
过往的片段,让他看得目眩神迷。
等睁开眼时,看见一个拳头大小的泡影落在掌心里,上面掠过的光影不像是他的过往。凝眸细看,不禁大惊失色,那是钟火山下广袤的神秘空间。
这时候,一道亮光闪过,龙睛缓缓睁开。
凝视龙睛的时间里,林晋渐渐感觉到龙睛在呼唤自己,它在那个漆黑的场所一遍又一遍地向林晋发出简短的讯号,讯号的含义不得而知,但其上依附的情绪却强烈而具体。那是一种召唤,召唤林晋向它走近,向它询问什么。
询问什么呢?毫无疑问,龙睛,或者说龙睛的所有者想向他诉说什么,一个秘密?还是一个预言?
“预言?”耳边响起凤囚那令人温暖的声音。“预言这东西往往是真的。”
他把滞重黏湿的眼皮缓缓睁开,凤囚那张时常微笑的脸庞显现在眼前。
凤囚坐在地上,腿上裹着一层厚厚的黑布,依旧穿着那件衣裳,头发梳得干净利索,脸也洗得纤尘不染,明亮透彻的眸子轻轻落在他身上,笑意一直蔓延到眼睛里,传递给眼前的人。
林晋不由得一笑,没法不笑。再次见到凤囚,他才晓得,原来自己一直在惦记着此人。不可思议,不过是见了一次面而已。
“你刚才说了梦话,念叨了几声‘预言’,白夜他们出去打猎了,天刚亮不久。”凤囚微笑着说道,“谢谢你带来丹豹髓,我这条腿算是保住了。你先醒会儿困,早饭已经做好,适当活动后,再痛快地吃上一顿,吸收过量造化带来的不适感应该就能消解了。”
“过量的造化?”林晋愕然,“我是因为这个才有垂死之感的?”
“是啊。”凤囚微微欠身,把林晋身旁的毯子拉过去,叠放整齐。“造化这东西是天地间至宝至贵之物,除了光明顶琉璃宫那帮老家伙们,常人绝无能力消受。你倒是不同寻常,这么丰沛的造化,怕是老家伙们也难以一次性化解。好歹化险为夷,真是为你高兴。”
林晋长吁一声,扶着地坐直,身体里的那种死气弥漫的感觉已经消散一空,意念一起,体气便随之涌动,意念一平,体气遂落。如此一来二去,他发现自己已经可以无比轻松地驾驭身体里的能量。他试着內照,一丝灵智轻轻松松地便进入了海底,抬眼一瞧,漂浮在海面上的那朵火莲已经悄然绽开两瓣。
“这么不劳而获,总觉得像作弊一样。”他说。
“跟你想的一样。”凤囚把手放在叠好的毯子上,轻轻地抚摸着,抬头笑了笑。“我很小的时候就反感这种事儿,周围很多人,平时一副道貌岸然的模样,一到分发造化的日子,人人便露出贪婪可憎理所当然的神情,从来不去想这些造化是怎么来的,别人辛辛苦苦打坐修行,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东西,他们就那么以堂而皇之的理由,毫不客气地勒索过去。”
“所以离家出走,到处乱逛,当过伶人,成了高空行走大师。然后带领一个因同一个原因相聚而成的队伍,在迷宫一样的森林里寻找出逃的路径,革命小分队似的,始终顽强,不服输,不信命,直到今天。”林晋笑着说。心里想,普通商人的家庭可不会分发造化。
“啊,可不是嘛,人生前三十年就是这么过的。”凤囚把毯子放进身后的架子上,抓起靠墙放着的一个拐杖,站了起来。“出去走走怎样?”
离洞穴三四里远的地方横躺着一条河流,不很宽,若小心避开水势湍急的河段,普通人凫水就能游到对岸。岸边生满青枫,时而可见几只磨盘大小的红色巨鸟在林子里踱步,鸟儿尾巴很长,羽毛像是烈火,走路时,昂首挺胸,气度非凡。
红色巨鸟消失在林间后,不一会儿,一头黑色的大兽慢蹭蹭地走进林晋两人的视线里,大兽肚子稀瘪,体毛脏得不成样子,只有一双三角形的眸子在眼缝里时而亮出精光,之所以看出那眸子是三角形的,自然是从三角形的眼眶推断出的。
大兽明显嗅到了什么气味儿,直起脖子仰天长长地叫了一声。叫声有些像狼嗥,但音色远比狼嗥宽阔,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如一股飓风,滚滚穿过青枫林,一时间枫叶纷纷坠落,湍急的河流似乎都凝滞了片刻。
“这么瘦,像是饿了好几天了,恐怕打不过大鸟。”林晋随手揪了一片枫叶,手指间转了几下叶柄,然后把它扔到河里。
“我看未必。”凤囚坐在一根木头上,伸直了伤腿,拐杖放在腿边。一直悬空漂浮着,也太耗费体气,不如拄着拐杖走路现实。此时的凤囚,脸上有着一股宁静,这种宁静应该只能从坐在轮椅上的年轻诗人的脸上看得到。
“未必打不过红鸟?”林晋双手抱在胸前,顺便感受了一下风向,把对龙睛、召唤之类的思索暂时抛开。
“哪里。”凤囚笑起来,“这头野兽未必对红鸟有胃口。”
“那咱们动手?”林晋陡然有些紧张,这里除了红鸟只有两个人类。
“两个赤子境上品的修行者,在一头瘦得皮包骨头的野兽面前落荒而逃,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凤囚慢慢把拐杖抓在手里。
“我不说,你不说,谁会知道。”林晋望见大兽的脑袋缓缓转了过来,三角形的眼睛慢慢睁开,恍然间,两人仿佛被两道杀气腾腾的光柱锁定住了。
“高见。”凤囚拄着拐杖站起来,手持拐杖指着远处的大兽,遗憾地道,“其实,它没什么可怕的,不过,我觉得,咱们还是,跑啊!”
两人大喊一声,争先恐后地往枫林深处跑去,凤囚一蹦一跳,林晋脚不沾地,两个家伙一口气跑出老远,停在一个土坡前大口大口喘气,对视一眼,互相指着哈哈大笑,笑完了,先后一屁股坐在地上。
“喂,你跑得可真够快的。”林晋搂住凤囚的肩膀。
“那当然,我可不单单会高空行走,腿没瘸之前,被一头玃追得满林子跑,那家伙抓着树藤,飞得那叫一个快,我俩一个追一个跑,玩到天黑。”凤囚也攀住林晋的肩膀,笑嘻嘻的。
“怕倒是不怕那头大兽,只是,这么宁静的一天不想被破坏掉。”林晋靠在土坡前,脑袋枕在胳膊上。天空像是冬夜的剩粥一样,把冷清与肃杀凝结成团。隐约间,在冻云深处,似乎慢慢浮现出一个硕大的阴影,阴影在将要挤破云层时,却又悄然退隐。
“同感。”凤囚也摇头叹息,“以前连杀鸡都不忍心看,自打陷在森林后,天天看白夜剥兔子,渐渐的也习惯了。”
“喂,作为一个男人,这么心软可不行。”林晋说。他决定不把看到阴影的事说出来,或许是自己一时的眼花。
“心不得不硬时,恐怕会硬得连自己都觉得可怕。”凤囚语气有些冰冷。
林晋转过目光,在凤囚的眼角隐约看到一丝阴翳。莫名其妙的,他的心开始往下沉。
沿着一条荒草凄凄的小路走了约莫十分钟,不觉又到了河边。石块历历可见,自由自在地躺在河床上。天空的倒影在波光里辗转反侧,平添几分灵动。没有风,四周一片寂静。凤囚在岸上站了良久,忽然扑在水里。
“不来吗?”顷刻,凤囚的脑袋从水中钻出来,开心地笑着,冲岸上招手。
林晋捡起地上拐杖,想找个地方放起来。凤囚大声说,“别管那东西了,水里好温暖啊。”声音里饱含无限满足,无限依恋,好像那条河是母亲的怀抱似的。
林晋紧了紧背囊,想脱掉袍子,一想不知道要游多远,索性不脱了。慢慢步入水里,冰凉彻骨,说来也怪,一来到水里,瞬间就感觉到凉风贴着水面吹在身上。
他和凤囚一样,往水里仰躺,双臂朝后拔水,两脚颇有节奏地交替蹬着水,游了好一会儿,才追上凤囚。
“能记住这条河吗?”凤囚转过脸问,晶莹剔透的水珠从脸上滚落。
林晋瞅了瞅两岸,手搭凉棚向洞穴方向远眺,随后点点头:“应该能。”
“那就好。”凤囚如一条大鱼似的在水里完全放松,有些忧郁地看着天幕:“滚瓜烂熟地记在心里,沿着河一直游,游到筋疲力尽为止,或许就能柳暗花明,看到别样的风景,这就是我爱这条河的缘故,始终在流动,始终朝着一个方向不知疲倦地奔赴着,我称这个为河流的精神。”
两人半浮半沉,随着河水漂流。有时候,林晋微微侧身,把脸埋在水里朝水下探视,只见河流深处唯有一块块星罗棋布的石块,鱼一条都没有,甚至水草也不见一根,渐渐的,他感觉到一股奇怪的氛围,甚至感觉到荒诞,恍然间,像是在一条布满死亡气息的通道上空漂浮似的。
远处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哨声,是白夜在呼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