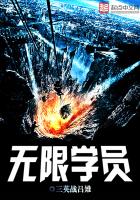确实二人都错怪了畏先,他本是有事来的,不过见祁玲仍在房中,不好意思说出来。反至看出两人都神情冷淡,才悟到自己讨了人家的厌。想要辞出,更恐这样匆匆来去,惹他们加倍不快。只可迳直向景韩道:“我有点事来求你帮忙,这事实不是我愿意,实在没有法子。”说着又吞吞吐吐的望着景韩,半晌没说出话,忽又转脸向祁玲道:“龙珍因为在家里闲着无聊,想在咱们公司寻些事做,非要我办到不可。”祁玲听了一惊,暗想龙珍本说嫁畏先以后要安居家庭,永与白萍避面,怎又想到公司作事?难道她又变了主意么?接着畏先又道:“我劝她不必来,她只是不肯。我又说现在白萍出门,公司没人主事。只可等他回来再说。龙珍说只要到公司来有件事作,可以消遣时光,她既不在乎名义,也不在乎薪水。叫我先来求景韩设法给个位置。她要在晚上我回家时听信儿。你看她不是异想天开么?我被她缠得没法,只得……”祁玲正在思索龙珍是什么意思,景韩已笑道:“我明白这是你新的太太和你爱情深厚,不愿有一刻分离,所以才想出这同出同归,成天厮守的法子。我认为是一件好事,应该成全的。那么明天就叫她来,在总务股帮你办事吧。我可以替白萍答应。至于薪水可要等白萍回来再定。”祁玲听景韩自然允许,想拦已来不及。畏先却皱眉:“请你别叫她跟我同房办事。”景韩道:“为什么?你是避嫌疑么?”畏先摇头道:“不,不。我是不愿意。这原因祁姐知道的。”景韩笑道:“夫妻同房办事,还有什么不愿?你不必装假,我就这样定规了。”畏先苦着脸儿向祁玲道:“我这才叫真正的无可奈何,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这还得谢谢景韩。”说完便慢漫走出去。景韩大笑道:“你见害神经病的么?畏先就是。他又替太太谋事,又好些不愿意。这是什样原故?”祁玲道:“我方才不是告诉你了。畏先对于龙珍,实在是大勉强。而且又受不了龙珍的那种肉麻劲儿。他每天陪龙珍去玩,已经头疼了。如今再让他们同来同去,寸步不离,不是。”景韩笑道:“我就因为方才听了你的话,才和畏先开这玩笑。算罚他惊动咱们的罪。”祁玲道:“你只顾和他玩笑,可忘了白萍那一面。龙珍当初和白萍也有过密切关系的。如今用她来作事,定要常和白萍见面,恐怕有很多不便。”景韩道:“这样我倒莽撞了。好在龙珍已是钱太太,又在畏先身旁作事,也没什么?”祁玲也没再向下说,但心中只觉龙珍到公司来,是十分可怕的事。至于如何可怕,却想不出所以然来。这时景韩才开了电灯,窗外已完全黑了。祁玲便要回家。
景韩对她向来都很洒脱,不似小儿女那样缠绵依恋。但今日有了进一步的灵肉结合,竟而舍不得她走,苦苦留住。说着话儿,动手动脚起来。祁玲发恼道:“你还闹呢。方才叫畏先吓得我心跳口喘的,差点儿没窘死。你趁早躲开,要不我又走了。”景韩想了想道:“那么咱们就出去吃晚饭,好不好?”祁玲答应了。二人便出了公司,直奔一家饭馆。用罢晚餐,祁玲又要回去。景韩还不放她走,定要再寻个地方谈谈。祁玲问他上哪里去?景韩道:“你不必问,随我走吧。”祁玲跟着他在街上步行。走到一家旅馆门前,景韩低语道:“咱们进去寻一个朋友坐坐。祁玲才料到景韩有此一举。
她虽然很能克制自己,但是中年妇人,对于性欲,任凭如何淡薄,终经不住挑逗的。祁玲本已久旷,平日因善自排遣,还不觉有什么需要。今日在景韩房中,突然谈出了毛病,已把多年的情思都翻腾起来。无端叫畏先搅得半途而废,她便感到被身体变化压迫得难过,急欲回去安静地睡一觉儿。但是景韩挽留不放,吃饭时又喝了几杯酒,更惹得心里热辣辣的不能自持。偏在这时侯,景韩将她领到旅馆。祁玲虽明知他不是寻朋友,也不说破,竟点点头儿随他上了楼。景韩向茶房要上等房间,开门进去。祁玲仍不开口,也不看他,只默坐在椅上。等茶房送进茶来,又行出去。景韩关好了门,脱了外衣,笑道:“你干么发怔?躺下歇歇吧。”祁玲道:“我坐着好。你的朋友呢?”景韩道:“我的朋友就是你。”祁玲道:“我……你把我领到这个地方来作什么?”景韩走过抱住她道:“你还问我?这里可不怕谁来搅了。咱们安安静静的住一夜吧。”祁玲道:“那可不成。我跑到旅馆来住夜,成了什么人了?快放我走。”景韩知道她是故意做作,拥抱着只管缠磨。祁玲也觉情不自禁,又因自己若在外面住夜,定惹张家人疑惑,最晚也得十二点前后回去。时光宝贵,不可虚度,便也半推半就的,装作娇怯无力,不大的功夫,就被景韩抱到床上去了。以下的事,不必细表。到二人从帐中出来,已是十二点多钟。一个体倦神疲,一个粉褪发松。祁玲立到装台镜前,从手皮包中拿出化装物品,徐徐收拾头面。却望着镜中自己的影儿,只抿嘴作得意的微笑。她不特得到满足,并且感到将来的幸福了。景韩望着她理妆,忽然想起她向来出门,皮夹里不带化装用具。因为肌肤细白,天然清洁,用不着常常修饰。今天竟破天荒带了这些梳镜粉膏之类,居然备而有用了。怎这样巧呢?又一转想才明白她今日来访自己以前,便已有心。虽然未必要作主动,但已预备不拒绝我的要求了。景韩想着正在销魂,祁玲已收拾完了,便要回家。景韩又拉住温存一会,才付帐同出旅馆。祁玲自己坐车回去。
景韩返了公司,到寝室坐下,忽见畏先又过来了。景韩纳闷他这时还在公司作什么?畏先已嚼嗫着说道:“景韩先生,我等半天了。”景韩方要问等我作什么,畏先已低声道:“贱内因为您给她事作,她感激极了,正等着谢您呢。”景韩暗想何必定要今晚来谢,难道不能等到明天么?但这时畏先已向外招手,就见龙珍已走进来。景韩还是初次看到龙珍,不禁吓了一跳。觉得这女子真够丑了。谁想到她能和白萍那样漂亮的少年会有过关系呢?这时龙珍已向景韩鞠了一躬道:“多谢先生帮忙。”景韩自然客气了几句,又让坐谈了一会。龙珍忽然笑道:“我有一件事求先生,我因为急于作事,想明天到公司便有正式的职分。您现在可以先分派么?”景韩因为已经答应了,不便反悔,便道:“请钱太太到钱先生房里,作收发员吧。”龙珍道:“谢谢您。不过我希望作些比较劳苦的事,可以锻炼能力。并且我还有件不合理的请求,就是希望离开畏先,独立作事。倘若在畏先手下,也恐怕同事背地里说闲话。”景韩想了想,觉得她的道理也对,便道:“若是钱太太想独立作事,我们公司有几个女演员,另住在后面宿舍,那宿舍还缺个女管理员。钱太太不嫌麻烦,就请担任这职务吧。”龙珍听着面有喜色道:“这职务正合我的兴趣,那么作管理员应该到公司来住吧。”景韩知道她和畏先燕尔新婚,恐怕叫她到公司来住,过于不合人情,便道:“也不一定。要不在这儿住,早晨来晚上走也可以的。”龙珍道:“不,我很愿意住到公司。管理宿舍若不整天工作,还有什么效力?”畏先听了这话也觉深出意外,暗想她方才并没提起这层,怎现在突然对景韩说出这种话呢?景韩也惊诧她在蜜月中居然和丈夫分居,不知是什么意思?但照规矩女管理员是应该住在公司的,也不能反驳,只可说道:“这本是可以随便。请您二位商量。在这里住不住都行。”龙珍道:“明天我就带行李来。实行作事好了。”景韩只得点头应允。畏先始终并未插言。须臾龙珍辞出,畏先便跟着走了。景韩仔细一想,才诧异龙珍竭力要求移来,其中必有原因。或者她厌恶畏先,不能在家中同住,所以藉此避开不过当初又何必嫁他呢?又想到白天自己允龙珍到公司作事,祁玲已认为不妥。现在又允她到公司来住,恐怕祁玲更要反对。这只怪自己面皮太薄,对女人的要求,无法拒绝。好在是派她作女宿舍的事,和前面的人交涉很少,更不会常和白萍见面。还未必有什么意外事发生。想着也没甚深思,便丢开这事不理。
到了次日。龙珍午前便来,带着随身箱饰。景韩便领她到女宿舍里,指定了住室,又给女演员们介绍了。龙珍就兢兢业业的作起事来,半天工夫,居然把女宿舍整理得大改旧观。景韩倒颇为佩服龙珍作事的精神能力。以为既有这许多长处,足可把面貌的丑陋抵销。畏先得这样内助,倒是福分。等白萍回来,总可以给她定几十元薪金,夫妇互助的生活下,很容易造成安乐家庭呢。这一日祁玲没有到公司来,还不知这个消息。
又过一日,祁玲在家中接到淑敏寄来一封短信,报告和白萍正在天津住着,每日度着游戏生活。除了听大戏看电影上舞场吃馆子逛马路以外,简直再没有好玩的事,觉得很少意趣。又责问祁玲为什么失信不去?等她回来,定要严厉对待等语。祁玲暗笑,你俩这几日直是预支蜜月的享受,还不知怎样陶醉在情海里呢?这都是我失信造出的功德啊!想着便要把他俩的消息通知景韩,于是午后又奔了公司。见着景韩,将淑敏来信给他看了,二人说笑了一会。景韩才提起龙珍的事,祁玲大愕道:“你怎这样胡乱安排?叫龙珍进来作事,已然欠妥。为何又许她住到这里?景韩道:“因为她说的话很有理由,我不好意思拒绝。她进来任职这两天,有很好的工作。和女演员也全融洽。我想她或者是真立志作事,未必有什么可愿忌的。你所怕的只是那些事,并不成问题。因为她已是钱太太,白萍也就快是淑敏的丈夫了。”祁玲道:“我还疑惑,她便真要作事,可寻的职业也多了。何必单向这公司里挤?来给白萍手下作事呢?”景韩道:“提起这个,我还想起一件事,昨天夜里十二点多钟,我忽然精神兴奋,知道短时间里未必使能入睡,想要把一张演员表要新更订一下。因为演员表的草底几在白萍房子里,就带了他房门的钥匙,过去把门开了。在写字桌的抽屉里,寻着那草底儿。联带又看见一张新置道具的价目清单。便坐在椅上,核算出总数。一共耽搁没十分钟工夫,就走出来。想要把门重行锁上,哪知原插在锁孔上的钥匙,竟不见了。我以为掉在地下,忙开了院里电灯,仔细寻觅,却是踪影不见。我又怕自己记错,或者随手带进房去。随又进到里面寻觅,每个地方都翻到了,仍然没有,急得我别提。因为白萍房中有很多重要东西,钥匙万丢不得。只可坐定,仔细回想,开门时的情形。又记得确把钥匙放在锁孔中,而且那钥匙是门上所用,形体很大,约有三四寸长。又是铜质,便落到地下,也听得见响声。丢在什么地方,也很容易寻着。怎会这样不翼而飞、毫无踪影?因此我才想到或是我进房中的时候,有人从门外经过,顺手从锁孔上将钥匙取去。本要唤起全公司人询问。又想平常人谁也不会无故的把钥匙偷去。若真有人偷了,那必是早已处心积虑,将有所图。好容易今日得手,怎能一询问便退还出来?于是我决意不声张,以免打草惊蛇。先悄悄的在这几道院里巡查一遍,见前后院的人已都睡了,及至走到东跨院的女宿舍,看见只龙珍的房里还亮着灯。我想要进前从窗孔看她睡了没睡,哪知才进去几步,就见房里把灯灭了。我只可退回。又巡查了半天,也没一点迹兆。直到今天早晨,还在白萍房里寻觅一回,仍然没有。你说这事怪不怪?”祁玲听了,也觉惊异道:“我听说公司款项,向来都存银行。只会计那里有些零星小款。白萍的住房更不会有钱。再说白萍本身又没有金银财宝,便是有着你所谓的要件,也不过一些纸头,何能引人生心?若没人生心偷盗,就不致先偷钥匙。据我想,你或者记错了,把钥匙随手丢在那里。过后想不起来,才闹这玄虚。”景韩道,“我已经仔细追想,敢说绝对没有记错。那钥匙十有八九是被人偷去。”祁玲道,“你既然说得这样确实,那么只可研究谁有偷的嫌疑。你以为龙珍嫌疑很大,是么?”景韩道:“我也不敢说一定。不过她来了两天,就出这个事。而且她和白萍以前又有过关系。”祁玲道:“可是她偷这钥匙作什么呢?”景韩道:“倘真是她偷了,自然有她的用处。”祁玲道:“不过这样偷法也太笨了。你发现丢了钥匙,自然要特别注意访查。她若去用钥匙开白萍的门,岂不是自投罗网。何况这洋式的锁,没有钥匙根本就没法再锁。势必把旧锁门作废,另换新的,才能锁上。那时她偷去的钥匙更没用了。我且问你,昨夜从发现这事,白萍的房门一直开着么?”景韩道:“因为没法锁,我就在那房睡着看守,到早晨我才出来。这白天里耳目众多,谁也不敢偷着进去。今夜我还得住在那里。等明天换了新锁再说。”祁玲道:“着呀。这是很容易料到的。失去钥匙以后,就得有人看守。等没人守时,又换了新锁。旧钥匙永远是废物。我不信有人偷。必是你粗心,没有仔细寻觅。而且两只大近视眼,就是东西明摆在面前,还许瞧不见呢。走,走,我跟你寻寻去,省得这样失惊道怪的,自己吓唬自己。”说着就拉景韩走出,到了白萍住房门外。
景韩先把虚掩的门推开,“你瞧,这门是向里推的。昨夜我开了门,就推开一道缝儿进去。出来时把门拉上,扯摸钥匙,就没有了。”祁玲先把门内外的地面细看了一遍,又进房去把里外闻各处都翻了,仍是毫无发现。才走出来,立在院中发怔。景韩道:“你现在可信了。我费了好几点钟工夫。没一处不看到。”祁玲忽然心血来潮,抬头问道:“在你没开这门以前,钥匙放在哪里?”景韩道:“从白萍临走那天,把钥匙交给我。我就随手放在身上西装裤后面口袋里。两天工夫,我虽然觉得一坐下就格得不舒服,可是一直没换地方。直到昨夜开门,才取出来。”祁玲道:“我记得你向来喜欢把钥匙等小物件,塞在裤袋里。你再想想,别是开门以后,不自觉的把钥匙又从锁孔拨出,放回原处了吧。这是习惯的动作,或者你没注意,试摸摸裤袋看。”景韩道:“不用摸,我昨天已经摸过了。”祁玲道:“你再寻一下,这是没准儿的事。也许裤袋破了,把东西溜在裤腿的夹层里去。”说着又指指景韩的裤子道:“这也不费事,一伸手就成。”景韩笑道:“我昨夜穿的不是身上这件。这件是今早新换的。”祁玲道:“那么昨夜穿的那件呢?”景韩回身举手一指道:“那不是。昨夜我在白萍房里合衣睡了一觉。把裤子都弄得褶绉了。所以今天脱下放在院里晒着,等烫一烫再穿。”祁玲看见墙角扯着一根铁绳,裤子晒在上面。便走过去,伸手向右边裤袋中一掏,忽然啊的叫了一声。再缩出手来,景韩竟瞧见她手上拿着一件黄色物件。忙赶过去一看,不禁大为吃惊,原来竟是那把遗失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