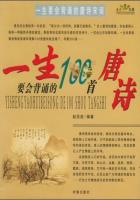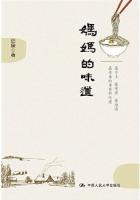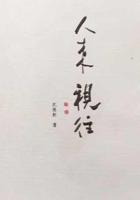石藤的聪明,使他作为这戏剧的“导演者”,在孩子们之群中出现了,——而马兰又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呢?他雄伟,壮健,并且有光明灿烂的灵魂;他像一个骠骑,一个武士,不,一个将军!
“马兰,”石藤把他派定了:“你就做一个将军吧!”
“振枢做新闻记者,——”他接着说;“你们要齐齐整整的排成一列,学着马兰的兵队固有的驯服与遵从;听着,听我的指令!……汉章做国王,那末,杨望呵,来吧,我要你做马兰的勇猛的兵队,还有陈岳、吴鹿、吕祖贻——够了,马兰的兵队不能过分的多的,过多了他们就难免要变成骄傲而且无用!那末,绍通做民众团体的代表,而朝征做长夏城的怀有二十世纪的战斗热情的市民,……”
当那排成了一列的行伍分散之后,马兰接受了汉章国王的意旨,随即对他的守御长夏城的兵队下命令,——“马兰将军统率下的将士们,”他挥动着他的竹制的指挥刀,开始了第一声的怒吼;“为着汉章国王的尊荣,你们必须从长夏城的前线立即撤退!……撤退呵!……”
马兰的兵队骚乱了,波动了,在长夏城的灰色的低空中发出了一片沉郁的噪音。
马兰下了命令,乘着飞机,——飞机“啪哒—啪哒”
的叫了一阵,到汉章国王那边去,向汉章国王复了命。而马兰的违反命令的兵队们,却在背后切切的低声私语,——“我的身上有三分之二的血和肉,是长夏城出产的葡萄酒所化成的,我的全身,正充溢着长夏城的泥土的潮湿的气氛和香味,而现在,我亏负了长夏城的守士的尊荣的名目,为着严守马兰将军的命令,长夏城哟,我要把你远远的抛弃了;我空应许了对于你的守护,——我对于你的守护的应许是空的!……”
“我的兄弟们,请不要笑我叹息,消沉,我的确衰丧,无力,不能趁这时奋发,振起,不像长夏城的温暖的气息所孵成的雄雏!……”
“那末,这一瞬的时间过后,我们埋在长夏城的深邃、富饶的酒窖将被发掘,骁勇的仇敌要在长夏城的最高的晒台上,高擎着他们的荣耀的战旗,……”
他们说着,一个个陷入了痛苦的深渊,暗暗的悲泣着,用手掩盖着自己的颜面,而长夏城的无数千万的市民们,却像将被赶赴屠场的羊群,惊慌了,惶乱了,正在作着绝望的祈求,——“主呵!我祝祷你的神勇,你的壮健,你的全能;你给我们以铁的援助吧!负心的马兰,枉费了他的食具,他的长靴,他的金黄色的庄严的戎装,为着逃命,将率领他的兵队远离我们而走了!——主呵,你赐给我们以神圣的力,……千员的战将,百万的神兵,……”
他们的祈求是获取了;所谓神圣的力,也不过止于解脱他们的危难,使他们在一种强固的信念中生存,——长夏城的胜利的战局,既经奠定,而使长夏城的市民们从沦亡中获救的倒不是主的神将,却是日常在长夏城的街道上往来出入,为他们所熟习的一队极平凡、极普通的兵队。
他们再也不是马兰的兵队;他们的勇敢的行动,已经越出了马兰的命令所制御的圈围。
现在,汉章国王的身心,正为这突如其来的长夏城的战报所震憾,——“坏了呵,坏了呵!”他惊骇得像为山间的野兽所威吓的女儿,混身只是簌簌的打颤;“马兰的兵队闯了祸,马兰的兵队竟然敢于走入敌人的哨兵所密布的田野,惊扰了敌人的安静的营幕,使他们以狮子的雄姿,激动了忿怒之火;他们将卷土而来,把我的锦绣的河山裂成粉碎,——我在逃亡的途中,也要咬牙,切齿,永远记得马兰所给与我的罪累!”
他随即把马兰叫到面前,严厉地喝着,——“马兰,现在要看你能不能补偿你自己的罪过,你必须立即到长夏城的前线去,去制止长夏城的守士暴乱的行为,使这些——王国的祸患之种们,在三十分钟之内,一无遗漏的从长夏城的界线向外撤退!要不是这样,我赐给你一把利刃,你必须用这利刃在回来的路上自刎,因为我再也不愿会见你的凶恶的面颜!”
马兰的飞机又“啪啦——啪啦”的叫了起来;马兰的飞机披着阔大的银灰色的翅膀,下降了;马兰以绝对尊严的将领的权威,出现在长夏城的守士们之前。
——不呀,马兰的尊严,还是缺少得很,他必须走进他的兵队在长夏城的郊外所张挂的营幕,然后,他看见他的兵队一个个从脸相上消失了过去下属对上官的狗一样的驯服与遵从——他们正像勤劳的工蜂,热烈地搬运着弹药,筑着堡垒,挖着濠沟,擦亮着枪刺,一队代替着一队的开赴前线,去应付那必死的决战;他们已经发狂了,他们所争取的是火线上的死亡率的九与十之对比,是九十九失败之后的一个胜利,而战斗的火是炎炽地燃烧起来了,他们喝醉了仇敌之血,正覆盖着白热的炮火在做梦……马兰,他必须发现了自己的职权之丧落,他就是依据着山神的金身出现,也不能再在这叛逆的部属中重复竖起原有的尊严,然后,他离开了他的队,——为着找寻他的疾苦的灵魂的避难所,他独自走进了长夏城的街道,陷入了长夏城的盈千累万的市民的重围,——长夏城的市民带着从死的劫难中重又安然地归来的喜悦,用着讴歌赞叹的歌舞者的热情在迎接他们的勇敢的战士——他们的战士的唯一的领袖,马兰将军,……看呵,倾城而出的市民们看呵!他没有护卫,不避危险,太阳在他的赭褐色的颜面上照耀着,他显得特别的壮健而且尊严,人类的高贵的热血在他全身的脉膊里奔驰,凭仗了他的力,长夏城的伟大的战功建立了,后世的子孙们,将在那花岗石的纪念碑上指着他的尊荣的名号,他们要说,马兰遗给了我们以镇慑一切仇敌的神勇,如今我们一个个都依据着他的壮健的雄姿长大了,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灿烂的光耀去制御宇宙间一切的灾殃,一如符咒之制御不可知的邪魔,因为马兰的灵魂以一化百,以千化万,他在我们的躯壳中潜隐地长大了,他影响于我们的身心和容貌,正如我们的父母所传授的血缘!……看呵,倾城而出的市民们看呵!他以中世纪的骑士的神勇,耸身越过了长夏城的街道上为应付战争而设置的障碍物,沿着那静止如镜的城河的岸畔,在铁制的河栏的旁边,威武、沉着的走着来了,长夏城的潮湿而又馨香的柔风拂动着他的衣襟,露出了里面的红色的织绒,愈加显见得他的戎装的庄严和尊贵;他的面孔带着为巨深的忧患所冲洗的战斗者的沉郁和悲愁,但是他坚决,镇静,没有一种外来的力能够动摇他的眼睛所放射的每一根钢的光芒;他一定为着视察长夏城的战地,因而走出了他的深远而无从臆测的决胜千里的幄帷——他扮成一个小卒,一个军曹,要用低下的外衣来掩蔽他的远射的光辉,从而忘记了自身的伟大,不知这盈千累万的市民们所欢呼迎接的来者,正是长夏城的守士的唯一的领袖——英勇的马兰!
盈千累万的市民们,以长音节的呼声高喊,——“马兰将军万岁!”
“汉章国王万岁!”
这声音一阵强似一阵,构成了奔腾的巨浪,冲洗着长夏城的灰暗的全貌,长夏城的一间间、一座座的平舍与大厦的屋顶,犹如加添了贵重的宝石,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如今长夏城遇到了极度的紧张,遇到了为空前未有的喜悦所激起的痉挛,它停止了全部的交通,停止了脉膊的跳动,用窒息的胸怀去拥抱马兰将军的绝对的尊严。
——不,马兰的尊严,还是缺少得很,他记得,他怎样的走进了他的兵队在长夏城的郊外所张挂的营幕,并且,他清楚地瞧见,他的兵队一个个从脸相上消失了过去下属对上官的狗一样的驯服与遵从——他们正像勤劳的工蜂,热烈地搬运着弹药,筑着保垒,挖着壕沟,擦亮着枪刺,一队代替着一队的开赴前线,去应付那必死的决战;他们已经癫狂了,他们所争取的是九十九个失败之后的一个胜利,而战斗的火是炎炽地燃烧起来了,他们喝醉了敌人之血,正覆盖着白热的炮火在做梦,………长夏城的战祸是再也无从遏止了,——而汉章国王的命令,却使他的内心起着深隐不白的悲苦和惊惶,——“马兰,现在要看你能不能补偿自己的罪过,你必须立即到长夏城的前线去,制止长夏城的守士的暴乱的行为,使这些王国的祸患之种们,在三十分钟之内,一无遗漏的从长夏城的界线向外撤退!要不是这样,我赐给你一把利刃,你必须用这利刃在回来的路上自刎,因为我再也不愿会见你的凶恶的面颜!”
马兰困惑,慌乱,暗藏着狼狈的心,逃出了长夏城的盈千累万的市民的重围。
他必须变换了原有的服装,躲进长夏城的一个最下等的旅馆,然后,他准备着在第二天的早上从长夏城出走,向着远远的、远远的地方逃亡。……他必须以仓惶、失措的行踪,作为一切消息的探采者们所需求的秘密而被发现,然后,他再也无从逃出,新闻记者和民众团体的代表们包围了那奇迹的旅馆,拥入了他的卧房;在那灰暗、缺乏光线的房子里,新闻记者燃起了Kodak之火,用着最准确的镜头,去摄取马兰的神勇的容颜,一面录取了马兰的珍贵的言辞,用着特大的字粒在报纸上发表出来,使王国全境的人民们知道,马兰是怎样的以热烈而又沉着的情绪,为长夏城的胜利的战局之奠定而发言,——马兰,他必须对于眼前的情景作起更准确的权衡,他既不能回到汉章国王那边去复命,又不能从长夏城的险景远脱而实行逃亡,另一面,长夏城的狂热的市民们对于他的现成的爱戴和拥护,却又重重地刺激着他的麻痹的神经,使他的动摇偏颇的身心得到了强固的镇静,然后,他真的强健了,威武了,——他必须从逃亡的路上重又折回,回到他的部属所结集的营垒,双脚稳稳的践定了,践定在长夏城的勇敢战士所据守的火线上,然后,他真的强健了,威武了,他一面向着汉章国王竖起了反叛之旗,一面把长夏城的战绩作为一己所有的一样接在手上,……——当这一出戏剧终了时,石藤正有点困乏,他用着疲累的眼睛,严肃而又冰冷,分析着马兰一身所有的假造的英勇和尊荣;他解释着,——“兄弟们,这一出戏剧,也和别的我们所看的戏剧一样,它必定有所说明,它正在说明着马兰将军是怎样的卑劣无耻——”
但是他的解释立即中断了,他发见马兰失去了坚强自信的喜悦的笑脸,换上了羞惭,愧赧的面颜,——马兰的光亮的灵魂变成昏暗,他的眼睛凝固了,嘴唇颤动了,脸孔泛着恐怖的青色,面额上冒着一颗颗的、湿落落的冷汗,经过了一度痛苦的挣扎,他终于决然地从孩子们之群中向外逃奔,——孩子们骚乱了,惊慌了;他们失声的叫喊着,仿佛有一种怪异的力从空中下降,它伸长着凶恶的巨臂,要毁灭人类生命的平安的权衡,……孩子们一个个的追赶上去,而可怜的马兰正在这时候逃进了那沿着城河一带繁茂地生长着的竹林,——长夏城的整个市郊正为严冷的暮霭所笼罩,西边的太阳变成了一个充血的脓包,丑恶地,一片一片的霉烂下去,一些混杂在灌木丛中的村落,起着轻淡的炊烟,在低空中环绕着落叶的残枝,作着搂抱的调戏;仅存的绿叶失掉了反射的光泽,而夕阳的最后的一缕金光也已经绝尽,……晚上,人们点燃着搜索的火炬,由马兰的母亲作着带领,向着城河沿岸一带的竹林里突进,——马兰的母亲的哭声,顺着河水的长蛇一样的波澜,向着为黑暗的夜阴所覆没的远处荡漾;沉入了壮丽的夜景中的城河,正叹息着它的亘古不灭的悲愁,那苍郁的竹林,却变成了特别的诡谲而且深邃,它要一口缄闭了人类向着一切灾祸呼救的回声,学着一个奸狡的骗者之所说,“什么我都不响,然而什么我都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