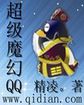邓小平坦率地指出:“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他又说:“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
今天,当我们来谈论农村大包干的成就时,会显得轻松且惬意。然而在当年,中国农民要迈过这道高高的历史门槛是多么不容易啊!
农村生产责任制的试验,先后在安徽省凤阳县和四川省广汉县取得了成功。
1979年,广泛流传于凤阳农村的一首顺口溜,最为生动、形象地表述了农民们喜不自禁的心绪:“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十年内乱,四川广汉县田畴不事稼穑,外地人只需用几十斤粮票就可以换走当地的一个大姑娘。广汉人以对饥饿最痛切的体尝和最果敢的实践勇气,在丰腴的土地上成为全国第一个用“包产到组”的形式种地的县。
1980年4月,当广汉县向阳镇率先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将摊子一分为三——乡党委、乡政府、农工商总公司时,马上成为震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爆炸性新闻。
这一举动无情地宣告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大锅饭体制在中国农村的寿终正寝。其后不久,中国农村被取消了20多年的乡、村政权机构得以恢复,它适应了新的生产形式的需要。
农村改革的潜流,日益在峡谷冲撞中迸发出巨大的诱惑力——
安徽、四川、贵州等地包产到户、包产到组的办法以最快的速度在全国传播并实施起来。
到1984年,中国广大农村569万个生产队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落实联产承包的农户达到18397.9万户,占总农户的96.6%。
从凤阳小岗一个队到全中国的500多万个队,短短六年时间,中国农民的前进步伐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
从1982年至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五年下达“一号文件”,向全国八亿农民郑重宣告:“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户家庭经营长期不变。”
土地是最容不得糊弄的——荒芜了就荒芜了,耕耘了就耕耘了。
一旦像农民尊重土地一样的尊重了农民,广袤的田野上便收获了顺应生产规律的硕果。
正是这一年,中国粮食生产创造了中国农业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纪录:全国粮食总产量高达4200亿公斤,人均粮食达到400公斤,第一次跃上世界平均水平;棉花人均占有量则超出世界平均水平。
六年前,邓小平就曾预言:“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被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想办法,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
农村经济改革这步棋,真正显示了中国政治家们懂透了中国农村。
至此,中国人有资格豪迈地向全世界宣告:“一个饥饿的时代基本结束了!”
随着1985年新年钟声的敲响,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二道帷幕被拉开了。
中央适时提出“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战略构思。
商品经济大潮首先在中国广大乡村冲决了千百年来森严壁垒、自我封闭的堤坝。
农村生产责任制的迅猛推广,有力地证明了它是现阶段发展中国农村经济的一种十分有效的形式。它消除了原有合作经济体制中的各种弊端,极大地解放了农民们长期受压抑的生产积极性和生产潜力,促使农业开始从自给半自给的小生产模式向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大农业转化。
随之,大量剩余劳动力和剩余资金的涌现,刺激农村的多种经营迅速崛起:兼业户、专业户、重点户等如同雨后春笋遍布乡村城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们,终于开始挣脱“黄土地”的束缚。
这是中国农村发展道路上继土地经营权改变之后,向产业经营权冲击的又一次重大拓展!
农工商协调进步,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共同发展,在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的进程中,乡镇企业当之无愧地唱起了“主角”。
1988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到6495亿元,相当于1978年的全国社会总产值——这意味着在农村改革兴起的十年间,乡镇企业走完了新中国30年所走过的漫长路程。
这是不亚于1984年粮食大丰收的辉煌。
这是奔涌于希望田野上的第二个大潮头。
从几千年刀耕火种的黄土地上萌生一个工业文明——这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中国乡村的一场惊世骇俗的产业革命——她分娩出了一个中国的“第二工业”。
三百年前,英国为完成它的资本原始积累,曾野蛮地将农民们驱赶出家园。而今日中国,亿万农民却豪迈地义无反顾地从乡间汇入了工业化的洪流。
中国的农民是幸运的——他们第一次成为商品经济大海中的弄潮儿……
改革不容易,与改革共命运的农民企业家们更不容易。
让我们来观赏一组已成为笑谈的历史镜头——
卢志民,吉林省四平市红嘴子农工商联合公司总经理,一个看上去十分普通的农村青年。
有一次,他乘坐的小轿车被交通警察拦住。
“谁的车?”
“我的。”
“你啥级别?”
“没有,我是农民。”
“农民?农民坐啥车!”警察毫不客气地摘走了车牌。
卢志民确实没有级别。然而,他游刃有余地指挥着一个固定资产3500万元、年产值达4000万元的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有如一个没爹没娘的野孩子,缺少资金,缺少设备,缺少原材料,缺少高科技……却在广大农村奇迹般地成长起来了。
它顽强的生命力,包容在自身所拥有的优势上——
东莞模式——“三来一补”加工型的乡镇企业发展道路。凭借调整农业结构,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业,对于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具有普遍的参照意义,是一条必由之路。
1990年与1978年相比,东莞市经济综合指标年均增长21%,农村人均收入从193元提高到1359元,大大高于全国和广东全省人均收入水平,全市80%的农户盖起了款式新颖的楼房。
温州模式——靠商业活动起家并逐步发展为依托外地市场加工业的乡镇企业道路,摆脱了当地资源的限制,突破了地域性商业周转的范围,与全国性的市场形成网状结构,对于促进城乡商品流通发挥了不可低估的桥梁作用。
被誉为“东方第一大纽扣市场”的温州永嘉县桥头镇,1979年由一位弹棉匠从外地买回一批处理纽扣在镇上摆起第一个纽扣摊,一年之后,镇上卖纽扣的摊点发展到100多家;迄至今日,全镇已有800多个纽扣店、摊,全国300多家纽扣厂生产的1700多个品种的纽扣在这里均有销售。每天,除市面上有5000多人从事经营外,还有9000多人在外跑采购和销售,组成了遍布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流通网络,仅镇邮局每天收到的汇款单就多达10万元。商品的流通又极大地刺激了产品的开发,纽扣生产厂家也如雨后野蘑菇般从这片土地上冒出来。
苏南模式——吸收沪宁一线大城市技术力量发展的乡镇企业道路。由于历史渊源,大批城市科技人员和熟练工人下放在这些乡镇,适逢改革盛世,他们成为农村商品经济大潮中呼风唤雨的人物,这是一条城乡工业协作发展的新路子。
声震全国的“丝绸之乡”苏州市吴江县盛泽乡,凭借雄厚的纺织技术力量,丝绸产品远销至东南亚、欧美各国;全国最大的丝织品交易市场也设于此,年产值逾10亿元。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赞曰:“日出万绸,衣被天下。”
依托科技进步走入“全国十佳乡镇”行列的福州市洪山乡,1990年的社会总产值达到4.2亿元,比改革前的1978年增长了46倍。
1987年,属于农民的乡镇企业,总产值首次超过农业。
1990年,乡镇企业出国创汇达130亿美元,占全国出口创汇总量的23.8%。
时至今日,乡镇企业发展到2000多万家,亦工亦农的工人超出1亿人。乡镇企业创造的产值在全国社会总产值比重中,已三分天下有其一。
什么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如何消化十多亿人口的沉重包袱。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常常为经济起飞带来的城市人口膨胀和种种城市病而头痛不已。中国乡镇企业的崛起,乡村城市化的大趋势,则表明从马克思到列宁到毛泽东多少共产党人梦寐以求消灭城乡差别的美好愿望,今天在中国大地上已开始成为现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中央有关部门曾通过分布在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近300个农村固定观察点,对10938家农户逐户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是令人欣慰的——
87.4%的农户对农村改革感到满意。0.8%的农户持“不满意”的态度。在满意的农户中,90.4%的农户回答,满意的是“生产有了自主权”;57.2%的农户回答,满意的是“感到比较自由了”;51.5%的农户回答,满意的是“集市贸易活跃,买卖方便”……
从自然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过程、一个社会过程,还是一个农民自主意识日益觉醒的过程——邓小平深刻论证了这一“过程”的全部含义,他指出:“这几年进行的农村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
一位市长的话则形象地预示了一种壮阔的前景:“农村经济改革的总体构想是党中央作出的。但是,当亿万农民参与其中并得到了实惠,从而变成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为时,就汇成了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大潮……”
毫无疑问,农村改革的飓风,已越来越猛烈地摇撼共和国大厦的窗棂,必将大气磅礴地推动中华民族迈上现代化的征程……
艰难的起飞
在人类发展史上,国家的出现是以城堡为标志的。
城市的诞生——象征着人类步入了一个全新的文明时代。
城市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宗教、文化、教育、科技于一身,是生产关系最完整最集中的体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总体形象的窗口。
这些气势恢宏、耸立云霄的高楼大厦,无疑是现代社会经济运作的中枢神经。
这里集结着共和国80%以上的财富。
每一道门槛,每一枚图章,乃至每一纸指令、计划、报表、分析,都如同大山一般威严,不容置疑地操纵和指挥着华夏民族这部庞大经济机组的运行。
然而,这部机组出现了局部锈死。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农村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他睿智的目光又瞄准了城市:“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
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有一句名言:“理解现实总是准备变革的第一步!”
旧体制的弊端在哪里呢?
通过指令性计划分配资金、物资,以及多层结构的行政管理,是我国传统经济管理体制的两大支柱——这种体制的根本缺陷在于,排斥、限制市场机制,漠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经济活动中的巨大作用,因而窒息了社会主义企业的活力和生机。
让我们来讲述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往事:一家每年接受国家1000万元巨额亏损补贴的大型企业,向上级主管部门递交报告,要求将1000万元补贴款先期下拨,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保证当年扭亏,次年盈利。答复是:要把在年底拨给的补贴款提前到年初拨给,整套周密的计划就被打乱了,你们还是按原计划在每年年底照领1000万元亏损补贴算了。
似乎是一则“黑色幽默”。
可悲的是,在传统产品经济模式中,这种嗷嗷待哺、患“亏损贫血症”的企业俯拾皆是。
显然,一种惰性的病毒已侵入肌体的骨髓……
历史不容等待。
北京,终于拉开了大幕——
1984年10月20日——一个将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深刻影响和改变城市市民生活的日子——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出台了。
邓小平以战略家的口吻告诫全党:“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使社会主义企业和生产单位具有充分的活力。”
突破第一道坚冰的壮阔,也许已成为历史的陈迹。
1979年,以四川国棉一厂、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八家企业为发端,实行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试点改革。
同年7月13日,国务院颁发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文件;年底,全国试点企业扩大到4200家;次年,又发展到6600多家。
旗开得胜——无疑为中国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一片乱草丛中踏出了一条新路。
让利放权,给企业“松绑”,成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
在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转轨变型时期,最初的突破所焕发出来的冲击力和诱惑力都是巨大的。
沙市、常州、重庆、潍坊先后成为综合改革的试点城市。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在生产、流通、分配、金融、科技、劳动组合、劳动工资以及政府机构职能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革尝试。
敞开大门,横向经济联合打破了长期闭锁的部门(即“条条”)与地区(即“块块”)分割,企业开始按照经济利益来选择合作伙伴。
过去鲜为人知的厂长、经理们,成为频频曝光在社会大舞台上的风云人物——改革者被人们赞誉为时代的新星。
改革——是勇敢者的事业!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兴起于80年代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态势,重又呈现出20年代中国民主革命所开辟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
将农村的“包”字请进城。
首都钢铁联合总公司率先进行了“上缴利润递增包干”试点,成为全国最早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国营大型企业。承包六年,上缴利税累计达70多亿元,平均每年递增20%。
“承包为本”四个大字,不仅对首钢,对钢铁行业,而且对其他各个行业的企业都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到1988年,全国93%的大中型企业实行了下述多种不同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两保一挂;上缴利润递增包干;上缴利润基数包干,超数分成;缴利亏损企业利润包干或亏损包干;行业投入产出包干等。
实行承包经营,责、权、利关系十分明确,从而改变了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状况,使企业由行政机关的附属物变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同时,改变了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状况,激发了广大职工主人翁的责任感。
人们也许还记得《人民日报》刊载的一幅妙趣横生的漫画:西方资本家亏损了50万元,急得要跳楼;中国的一位厂长亏损了100万元,却可以说句极轻松极时髦的话:“交了学费嘛!”
时隔不久,中国人却从电视荧屏上看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几度审议《企业破产法》时异常激烈争辩的镜头:作为法人代表的厂长们赞同《企业破产法》,但强烈要求自主经营,抗拒“婆婆们”无所不在的行政干预;工人们同样赞同《企业破产法》,但强烈要求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有权自己选择厂长,当然厂长也有权选择工人。
显然,厂长们和工人们全都不再感到轻松——长期吃惯了“大锅饭”、端惯了“铁饭碗”的中国人终于吃惊地发现:那些经营不善、连年亏损的企业真的纷纷破产、倒闭,或被兼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