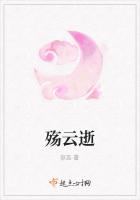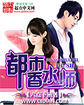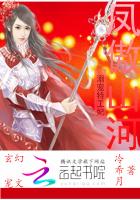中华民族是一个相当务实和崇尚功利的民族,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有记载历史的习惯,岂止是习惯,简直是执著,是癖好。为什么?有用。唐太宗说得好:“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时势的兴衰,社会的变迁,人事的关联,都需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历史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太重要了,尤其是对统治阶级而言。而印度古人没有书写历史的习惯,却讲得一口好故事,而且讲得执著,讲成癖好。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看来,真实的历史并不重要,倒是添枝加叶的故事更能表现创造力,更能让人的心灵得到愉悦和满足。所以印度自古盛产各种神话、寓言、故事、童话,假以时日,这种习惯形成风气,形成传统,这就是印度的民间文学传统。在中国,讲故事的风气不那么兴盛,所以神话传说虽有,却很少形成巨制,小说也出现得晚。这似乎与儒家的思想有关,其实也不仅仅与儒家有关,先秦的诸子百家,虽然也有不乏想象力的庄子之流,但占压倒优势的却是讲政治,说伦理,给统治阶级出主意,想办法,走上层路线,因而那些著作更文气,更具有官方色彩。印度古人也讲政治,说伦理,也给统治者出主意,但却发挥得厉害,更具有浓重的民间色彩。
下面,从四个方面来谈谈印度的民间文学传统。
(一)吠陀文学的民间性特征
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因为印度有些学者不承认吠陀文学属于民间文学。我们在这里要说明的是,吠陀文学具有明显的民间文学特征。
民间文学是具有特定含义的,是相对于文人文学而言的。一般认为,民间文学具有口头性、集体性和变异性特征,也有人认为在三大特征之外还要增加一个传承性。对此,刘魁立先生认为:“民间文学的创作则是动态的……这也是我们通常说的即兴特点。”根据现有的民间文学理论,我们认为,吠陀文学已经具备其所有的特征。
1.口头性
我们知道,吠陀文学作品是靠口头传播的,是师生间口耳相传保存下来的。正如金克木先生所说:“这些所谓经典长期以来只凭口头传授,甚至后来许多其他文献也是长期以口口相传为主。”印度上古有文字,但不大用来书写书籍,而古代的书写材料经常是树叶、树皮之类,即使书写了也很难长期保存。这是其口头文学发达的原因之一。吠陀文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得到长期的保存和流传,直到某一个时期被编定成书。
2.集体性
如果说吠陀文学作品都是有作者署名的,它们都是一些大名鼎鼎的婆罗门仙人,因而认为它们是出自文人之手的高雅之作,那就值得商榷了。的确,以《梨俱吠陀》为例,每一首诗都有作者署名,但仍如金克木先生所说:“《梨俱吠陀》的创作年代至今未能确定。这是古代的印度人民长期积累的集体创作,可能经历了几百年甚至千年以上的过程。”“传统给每首诗都署上一个仙人的名字,但这并不一定是诗的作者。”如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一样,虽然也署名为蚁垤(Valmiki)和毗耶娑(Vyasa)所作,但那仅仅是传承者之一,或者说是某个版本的编定者。
3.变异性
吠陀文学既然是口头传播,在流传过程中就一定会有变异,会有差别,这就是一些故事出现不同版本的原因。同一部吠陀中出现的神,描写并不一致,就更不要说在不同的文献中了。就拿《梨俱吠陀》中的天帝因陀罗来说,自相矛盾的地方就不少:一会儿在天上,是至高无上的神,一会儿又在地上,像是一个酋长;一会儿说他是陀湿多的儿子,一会儿又说陀湿多是他的敌人。所以,金先生说:“总起来看,这形象虽有矛盾,仍相当完整,是由氏族首长转变为奴隶主的第一个统治者的典型概括。”
4.传承性
吠陀文学作品具有传承性特征,所以有家族署名的情况,也就是说,某个家族世代为某一卷诗歌的流传作出了贡献。同时,这个家族的后期成员也许就是某卷诗歌的权威编定者。仍以《梨俱吠陀》为例,金克木先生指出:“印度传统认为这些诗是上古的仙人传授下来的。第二卷到第七卷是六个著名的仙人家族所传授,每一仙人家族有一卷。这六卷现在一般认为是比较古老的成分。第八卷是两个家族传授的。”但现在的问题是,一旦编定,其传承是否就中断了,就失去了其民间文学的特征。事情的结果的确是这样,但也不完全是这样。说是这样,因为自吠陀文献编定之后,被后世奉为经典,神圣不可改变,于是就相对固定了,尽管有不同的版本流传。同时,这些作品也从民众的口头上消失了,人们不再你传我我传你地背诵和讲述了,而是只有少数人偶尔搬出来运用一下。说不是这样,因为吠陀文学中的一些神,一些片断,仍然随着时代的演进和社会的发展在民众的口头上活跃着,丰富着,变异着。典型的如因陀罗,到后来还时常出现于史诗和往世书神话,也频繁出现于佛教和耆那教神话,他的故事也越来越多,地位也发生了变化。
以上情况说明,吠陀文学的确具备了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那么为什么仍然有印度学者不把它归入民间文学的范畴呢?原因也许有两点:第一,这些印度学者通常怀有宗教意识和宗教感情,认为吠陀是古代的圣典,是仙人的著作,自然不能与芸芸众生的口头传说同日而语。第二,由于这些古老经典的编定年代较早,较早地离开了民众的现实生活,离开了民众的舌头,走进了书面文学的圣殿,所以被排除于民间文学之外。
在中国也是一样,当我们追溯民间文学的源头时,一定要提到《诗经》,提到其中的“风”。
至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讨论印度民间文学时不应抛开吠陀文学,因为吠陀文学是印度民间文学的最早部分,虽然不是源头(因为唯一的源头是社会生活),但也是开山之作。
(二)史诗与印度民间文学
印度的两大史诗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这是西方、印度和中国学者们公认的,已经不必讨论。现在要说的是,印度的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在印度民间文学中的特殊地位。
我们知道,两大史诗在印度流传十分广泛,影响极其深远。它们虽然经过比较权威的编定,但却没有断送其民间文学的特征;它们被印度教徒奉为圣典,一直在民众中流传,甚至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流传。一句话,两大史诗在印度民间文学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文学现象。下面谈四点意见。
1.两大史诗对吠陀文学的继承
史诗是在吠陀文学之后形成的,对吠陀文学有继承,也有发展。所谓继承,是指它们与吠陀文献有一脉相承的血肉联系,一种割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当然,谁都不能否认,史诗的根本源泉是生活,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件。就拿《摩诃婆罗多》的主干故事来说,一般认为是根据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场战争演义而来的。这是其创新和发展的部分,是其区别于吠陀文学的部分。但是,史诗并不是仅仅有一个主干故事,而且其主干故事仅仅占全书的一小部分,那么,它们另外的大量内容是从哪里来的?来源是多方面多渠道的。有民间零散的故事、童话和寓言,也有一部分来自吠陀文学,来自对吠陀文学的吸收和发挥。它们对吠陀文学的继承关系大约可以总结为这样几点。
第一,它们从吠陀文学中吸收了许多神明,并降级使用。我们知道,在两大史诗里,已经出现了印度教的三位主要大神:大梵天、毗湿奴和湿婆。他们是史诗神话中的主要神明,尤其是毗湿奴,在《罗摩衍那》中化身为罗摩,在《摩诃婆罗多》中化身为黑天。三大神在吠陀文学中虽然有他们的影子,但并不引人注意。而吠陀神话中的一些主要神明统统都遭到降格。例如,因陀罗,在吠陀神话中是天帝,是拥有颂诗最多的最高神格。而在两大史诗当中,他被降低为第二流的神明,虽然也拥有巨大的威力,但却属于主神的附庸。其余的神明,如太阳神苏利耶、火神阿耆尼、水神伐楼那、风神伐由、死神阎摩等,都遭到同样的命运,变成了第二流的神。
第二,它们从吠陀文学中吸收了大量神话,并加以发挥。我们知道,《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都有一个特殊的讲述方式,即常常脱离主干故事而横生枝节,引来一些别的故事。这些故事被称为插话。而插话中往往有吠陀故事。例如,《摩诃婆罗多》的《初篇》第60~70颂,是“用《梨俱吠陀》诗体歌颂双马童”。而且这些诗节“不见于现存《梨俱吠陀》传本”。同样,沙恭达罗的故事、洪水故事、广延天女(优哩婆湿)的故事等,都先在吠陀或梵书中初见端倪,而后在史诗中得到丰富,变得完整。
第三,它们的一些主要角色直接继承了吠陀神的血脉。例如,《罗摩衍那》中的哈奴曼是风神伐由的儿子,故又被称为“风神之子”,《摩诃婆罗多》中的坚战是阎摩之子,迦尔纳是太阳神之子,无种和偕天是双马童之子,等等。这些最能体现史诗对吠陀神话的继承关系。
2.两大史诗与往世书文学
两大史诗的编定时间在一些比较古老的往世书之后,所以史诗中也多次提到往世书。但是,总体上讲,往世书比史诗晚出,有些往世书的成书时间晚到12世纪,有的往世书中提到了成吉思汗。而有的往世书中甚至提到16世纪印度莫卧儿王朝的皇帝阿克巴,这些部分显然是非常晚才补入的。
往世书里记载的主要是一些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比之史诗的早期部分要晚出,被认为是新的神话传说。金克木先生指出,“新的神话传说首先总是应时代的要求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也就是说,往世书也带有民间性特征。
那么,往世书与史诗的关系如何呢?首先,一部分史诗中的神话在往世书中得到丰富和发展。例如,在史诗《摩诃婆罗多》中,黑天作为大神的化身,以一国之君和般度五子亲戚的身份参加了大战,但在往世书(如《薄伽梵往世书》和《诃利世系》)里,他的出生、童年和少青年时期的故事被详细叙述。之所以说这是发展,是因为这样的刻画使得黑天的形象更加完整,更加人性化,更为百姓所喜爱。其次,史诗中的大神在往世书里出现了更多的化身,拥有了更多的业绩。如毗湿奴24次(主要有10次)化身为人和动物拯救世界苍生,湿婆及其家庭成员数次诛杀恶魔。这是往世书神话进一步社会化的表现,反映了人民大众除暴安良的愿望和社会安定的要求。最后,史诗中的故事被往世书采用,如《薄伽梵往世书》里就有罗摩的故事。还有许多小故事也被吸收进往世书。
根据以上情况,可以说,史诗对往世书具有开启作用。
3.两大史诗与印度虔诚文学
到了中世纪,梵语文学走向没落,各地方言文学开始兴起,史诗又开启了中世纪虔诚文学的大门。最典型的例子是苏尔达斯的《苏尔诗海》和杜尔西达斯的《罗摩功行湖》。前者描写的是黑天的故事,后者描写的是罗摩的故事。这两部书都十分受民众欢迎,流传的范围广泛而且深入人心,以至现在印度人提起《罗摩衍那》,并不是指蚁垤仙人的《罗摩衍那》,而是指《罗摩功行湖》。这两部中世纪的作品属于早期的印地语著作,而几乎同时代的其他语言文学也都在模仿史诗的创作,有的是翻译,有的是缩写,有的是根据某个片段加以发挥。这些作品都出现于各个地方语言文学的早期,对各个语言文学的发展起到奠基的作用。
4.两大史诗与近现代文学
两大史诗对印度近现代文学的影响也十分巨大,泰戈尔就曾经缩写过《罗摩衍那》,其他关于史诗故事的缩写、改写,或就其中片段扩写的书籍层出不穷,数不胜数,史诗几乎成了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这一现象说明,史诗千百年来已经深入人心。而深入人心的原因,分析起来主要有三:第一是宗教信仰的原因。印度大多数人信仰印度教,大神在人们的心目中是无比神圣的,他们每天要膜拜,要念颂,要记挂,要敬畏,因而大神的故事对他们最具有吸引力。第二是社会需要。社会上存在许多不平等,存在许多苦难和烦恼,需要排解,需要克服,需要安慰,史诗的故事和史诗中的教诲正是一剂良药。第三是史诗本身的艺术魅力。史诗经过无数人的苦心创作,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无论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可以从中得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三)印度民间文学的丰富性
鲁迅先生把印度古代民间寓言形容为“大林深泉”,是十分有道理的。而印度古人自己也用许多词汇来形容自己民间故事的繁多,有形容为“簇”(manjari)的(如《大故事花簇》),不仅繁多而且美丽;有形容为“湖”(sarovar)的(如《罗摩功行湖》,不仅宏富,而且清澈;有形容为“海”(sagar)的(如《故事海》《苏尔诗海》),不仅恢弘,而且无限。而“大林深泉”还给人一种烟雾缭绕,神秘深邃的意象。在人们的感觉里,印度那些净修林里的修士们正是在这种环境和氛围中驰骋想象,编排故事的。其实,到印度去看看就知道,故事随时随地都可以诞生。在青青的田野上,在碧绿的大树下,在低矮的茅棚里,在河边,在岩洞,在街道,在废墟,到处都蕴藏着许多故事。这就使得印度民间文学作品异常丰富。印度民间文学的丰富性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1.悠久的传统如一条长河
如前所说,印度古代的人们的确善于编故事,讲故事的人成癖,听故事的人也成癖。从吠陀开始,经过史诗、往世书、虔诚文学等,一直到近现代,民间文学和书面文学的新创作源源不断,犹如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
一方面,人们不断从吠陀文学和两大史诗中吸取营养,以其中的人物或故事要素为基础,不断扩充、完善和花样翻新;另一方面,又根据新的社会现实和新的生活经验积极创造新的故事。而新的故事在流传中又被不断扩充或改编,形成许多不同的版本。
2.一方水土产一方故事
印度土地辽阔,民族众多,而不同的民族使用不同的语言和文学,这在无形中就丰富了民间文学的创作。我们在印度书店里,在街道边,在火车站,在旅游点,到处都能看到那些关于史诗和各种往世书的小册子,有的有多个版本。至于古代的各种民间故事集,如《宝座故事三十二则》《僵尸鬼故事二十五则》《比尔巴尔故事》《故事海》(缩写本)等,更是比比皆是。多年以来,印度陆续出版了许多介绍不同地区民间文学作品的集子,每个邦的民间文学作品都有介绍。从这些集子就可以感受到印度民间文学的丰富多彩。
3.各宗各派都念自己的经
印度教派众多,印度教有印度教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而佛教除了在自己的典籍中容纳引进印度教神话传说外,也创造了自己的新神话传说,如佛传故事、神变故事等,而且还采集大量的民间故事汇集到自己的经典里,如《本生经》。耆那教也和佛教相似,也创作了本教门的新神话传说,也收集了民间故事。这样,印度的民间文学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四)印度民间文学的生命力
说到底,印度民间文学的生命力存在于民众之中。这是最终的结论。但是,还可以说得更具体一些,有以下诸端。
1.宗教信仰根深蒂固
由于宗教是印度人民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而民间文学自古以来就依存于宗教,并为宗教服务,所以,如史诗、往世书等宗教神话传说便可以获得与宗教同等的生命力。我们知道,宗教是一种精神的东西,是一种哲学,一种道德尺度和一种价值观。人总是有思想、有追求、有信仰,人如果没有信仰没有追求,人类就要退化,就要灭亡。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对宗教有一种依赖性。如果从社会的角度观察,宗教同时也是一种物质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社会现象,一种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人类社会产生之初便有了宗教,可以说,人类社会也对宗教有一定的依赖性,宗教始终伴随社会的发展而存在,直至人类社会的终结。既然宗教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那么附属于宗教的民间文学自然也就具有永久的生命力。
2.不断获得新载体
我们前面说过,印度的史诗等民间文学作品是后世人进行创作的取材之源,这就使印度的民间文学具有了不断获得新生,不断被注入活力的一次又一次生机。不仅如此,印度的民间文学还从古代起就与舞蹈、音乐、戏剧等结下不解之缘。印度的古典舞蹈表现的是史诗中的故事,六大流派没有例外。印度的民间舞蹈也大多表现民间故事,如阿萨姆邦的《比忽》舞、比哈尔邦的《洁塔·洁丁》舞等,都是有故事情节的,反映的是民间爱情故事和家长里短。而印度古代的戏剧典范《沙恭达罗》《优哩婆湿》等,也是根据民间传说改编创作的。
到了现代,电影电视事业发达起来了,民间文学作品又自然而然地走上了银幕和荧屏。翻开一部印度电影史,就会发现,印度最早生产的故事片是根据神话传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罗摩衍那》制作完成并放映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上演时万人空巷,直到现在还在反复播出。
还有,前面提到过印度市面上各种民间文学的印刷品,它们会成为能识文断字的老奶奶和母亲们的口头文学,传给下一代。
毫无疑问,这一切都助长了印度民间文学的传播,使它们不断获得新的传播方式。
3.口头性还将继续保持
新的传播媒体虽然强大,覆盖了全印度,但也不可能完全取代民间文学口头传播的渠道。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印度是一个人口大国,目前至少还有1/4的人口属于文盲,算起来能有二三亿人,比美国的总人口还要多,而且这种状况似乎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这么多的人不识字,给印度民间文学的口头传播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得出结论:印度具有悠久的民间文学传统,两大史诗在这一传统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印度拥有十分丰富的民间文学资源;今后,印度的民间文学还将保持旺盛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