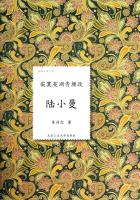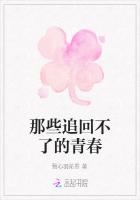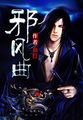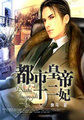在《楚辞》研究中,人们习惯于用近代形成的四大文类(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的观念,从“诗体文学”的角度思考问题,而对《楚辞》的“乐”性特征,或忽略不见,或予以否定,个别学者的论述,也多是从“诗—乐—舞”分离之后诗歌与音乐“关系”的角度进行的,并未从先秦时期的乐事活动和乐体文学的角度展开研究。
三代以来,“王者功成作乐”,敬神安民的乐事活动极为盛行。所谓乐体文学,就是指在以“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艺术活动为核心的乐事活动中创制、演习、传承的文学性文本。它具有“内容的综合包容性”、“功能的多重性”、“目的的实用功利性”、“情志的集体普泛性”、“效能的神秘性”、“运用的等级性”等特性,因而有别于后世意义的诗体文学,也与仅从诗歌与音乐“关系”的角度提出的“音乐文学”的概念不同。《诗经》、楚辞就是先秦时期在乐事活动中创制、演习、传承的乐体文学典籍。
下面试就《楚辞》的乐体文学特性,从三方面予以论证。
一、“兮”字句:楚辞“乐体文学”特性的重要标志
在先秦文献中,《楚辞》(本文仅指屈原的作品,下同。)用“兮”字最多也最集中。据周秉高先生对传统“25篇”屈赋及《招魂》《大招》《九辩》共28篇计15286个字的统计,“其中,兮’字用得最多,共出现了1038次,比总数的1/16还多,就是说,楚辞大约每16个字中就有一个‘兮’。”“楚辞用‘兮’,在先秦首屈一指。《诗经》305篇中只有61篇用‘兮’,即全书80%没有‘兮’字;而楚辞28篇中,只有《天问》一篇无‘兮’字。《诗经》7363句仅有280个‘兮’字句,不足4%;而楚辞2649句中有1038个‘兮’字句,竟占40%之多”。由此可见,“无论从密集程度还是总量多寡看,楚辞用‘兮’都远远超过了《诗经》!至于古籍中记录的先秦其他诗歌的用‘兮’情况,则是七零八落,不成体系,根本不能望楚辞之项背”。
关于“兮”字在楚辞中的作用,学者一般认为有如下三点:调整诗句节奏、“咏叹表情”和虚词功能。如,林庚先生说:“《楚辞》里的‘兮’字乃是一个纯粹句逗上的作用,它的目的只在让句子在自身的中央得一个较长的休息时间……它似乎只是一个音符,它因此最有力量能构成诗的节奏。”褚斌杰先生认为,《楚辞》中的“‘兮’字不仅用得更加广泛,而且在用法上与它以前也不完全相同。它在‘楚辞’中既起着表情的作用,又有调整节奏的作用,而像在《离骚》《九章》等散文化句式比较多的诗篇中,后者的作用却是主要的”。黄凤显先生认为,“兮”字“既有强烈的咏叹表情作用,也有调整节奏的功能。它是前两句与下文的两句之间的较为舒缓的停顿,是抒情语气的延长,又是诗歌节奏的一种调整”。另外,《九歌》句中的“兮”字还“具有某些虚词的功能……虚词和‘兮’字可以置换。如《东皇太一》中‘兮’字可以虚词取代,变成:‘灵偃蹇而姣服兮,芳菲菲其满堂。五音纷其繁会兮,君欣欣其乐康。’同样,《离骚》诗句也可换为:‘日月忽兮不淹,春与秋兮代序。惟草木兮零落,恐美人兮迟暮。’”这,都是从纯粹诗体文学的角度阐发其“作用”,因而才有人认为它或可省去不计,或可置换为虚词。
周秉高先生则指出:“楚辞大量用‘兮’是可以歌唱的标志。”虽然,“可歌之诗不见得一定有‘兮’字,但古籍中大量的记载确可证明:秦汉之际用‘兮’之诗可以歌唱,这该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而林河先生对沅湘地区民俗的研究也可佐证周先生的观点。林先生《〈九歌〉与沅湘民俗》一书中,引证了当地土家族、苗族、瑶族、侗族、汉族的民歌,其中就有大量的“兮”字歌。林先生指出:“沅湘间各民族至今仍十分流行的含‘兮’字民歌,应该就是古代‘兮’字歌的‘活化石’,而‘兮’字仍读xi音,也是一个铁的事实。”
我们赞同周先生的观点。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楚辞大量用‘兮’”,不仅“是可以歌唱的标志”,也是《楚辞》作为“乐体文学”典籍的重要标志。进而,我们还认为,从《楚辞》运用“兮”字的情况,不仅可以看出“楚辞各篇的曲调,彼此也不完全相同”,而且从其曲调的变化可以看出《楚辞》中存在着不同的文体。
他说,“大量用‘兮’不仅表明楚辞可以歌唱,而且还表明楚辞各篇的曲调,彼此也不完全相同”。他将表中所列“兮”字的分布归纳为“四式”:“句中式”、“单句末式”、“双句末式”和“少‘兮’无‘兮’式”,并对其歌唱的“曲调”进行了推拟。
虽然,对《楚辞》作品“曲调”(或谓“曲式”)的研究,并不从周先生开始,如,朱谦之先生《中国音乐文学史》中试图对其“声谱”进行考论,音乐史家杨荫浏先生从音乐史的角度指出《楚辞》中“至少已存在四种不同的曲式”,麻守中先生进而将其总结为:“民歌曲式”、“末尾加‘乱’辞的曲式”、“兼用‘少歌’、‘倡’、‘乱’的曲式”、“复杂曲式”四种。但是,综合来看,周先生从“兮”字的分布归纳出“其歌唱的形式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角度不同前人,结论客观可靠,给我们的启发更大。下面,我们参考诸家观点,从乐体文学的角度,对《楚辞》中包含的文体进行尝试性的分类。
我们认为,乐体文学作品,曲调不同,表明运用的场合也就不同,这就有了乐体文学中文体的区别。当然,这种区别如果从诗体文学的角度看,似乎不存在文体意义的差别,但是,若从乐事活动的角度看乐体文学作品,却有着明显的文体差异。依此,我们把《楚辞》作品的文体分为以下五种:
1.“舞歌体”,以《九歌》为代表。特点是:“兮”字在句中,“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类似后世的“歌舞剧”。周先生分析“句中式”的曲调特点是:“①基本相连;②‘兮’字两侧文字少、音节短,歌唱时逢‘兮’则气出而扬,达一高潮。此为《九歌》标准式,歌唱时可能呈‘安歌’、‘浩唱’、‘展诗’和‘容与’之状。”
2.“诵歌体”,以《离骚》为代表,包括《九章》《远游》和宋玉的《九辩》。特点是:“兮”字在单句末,是赵逵夫先生申说的“诵诗”类,但应是可歌唱的。周先生分析“单句末式”的曲调特点是:两句基本相连,因“‘兮’字两侧文字多、音节长,歌唱时大概呈现‘长言’、‘咏叹’之状”。也如赵逵夫先生所说:“单句之末带泛声的语助词‘兮’,使上下两句成抑扬之势;同时,这个‘兮’字使上句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独立性,从而同下句语气上形成似连非连的关系。”“上句末尾带‘兮’,读起来余音摇曳而语调较低、较轻;下句末尾不带‘兮’,而有韵脚,至句尾声音拖长,语调较强。这样就形成更为明显的抑扬之势,造成更为强烈的节奏感。”
3.“招歌体”(或称“呼歌体”),以《招魂》《大招》为代表。特点是:“兮”(“些”、“只”)字在双句末,“招”、“呼”、“歌”、“唤”为主,也有舞容。“此式唱时,繁音促节’,但毕竟‘兮’字作结,句末飞扬,余音袅袅,歌声显得尤其悠扬有力。如《论语》形容‘《关雎》之“乱”’那样:‘洋洋乎盈耳’。”
4.“问歌体”,以《天问》为代表。特点是:无“兮”字,“问”时也会拖长声调,似“歌”,但与上述三体区别明显。“《天问》373句,无一‘兮’字,或许不能歌唱,或许也能歌唱。因为《楚辞章句》云:屈原‘因书其壁,何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何’与‘可’、‘诃’均通。可’为‘歌’之古字,诃’也与‘歌’通。因此《天问》也有可歌之可能,其形式大概与《大雅》和三颂相似:缓慢、深沉。表现出一种郁悒、凝思的情态”。
5.“讲歌体”,《卜居》《渔父》属之。特点是:无“兮”字。它是乐事活动中讲述有关史事、传说的“史话”部分,也可谓“传说体”。“讲”时也或“歌”之,但与前三体已然不同。
二、“歌节”:楚辞曲式构成的最小单位
宋人钱杲之《离骚集传》指出,《诗经》“有节有章”,楚辞“有节无章”。与《诗经》“叠章复句”的形式不同,楚辞作品的最小的形式要素是“歌节”。
楚辞的“歌节”,最常见、最基本、最主要的是四句一节。虽然,因为研究者所依据的划分标准不同而对个别作品的划分产生了分歧,但是,“歌节”作为楚辞文体中本来就有的形式要素,四句一节的“常式”,还是大家认同的。根据王力先生的《楚辞韵读》,《离骚》《天问》《九章》等作品中的各章节多为四句,《离骚》《桔颂》全篇为四句一节。赵逵夫先生说:“屈赋中《九歌》以外的作品无论是骚体的还是四言的,都是四句为一节。”殷光熹先生《楚辞的歌节变化及其特点》一文也说:“楚辞的歌节,变化虽多(有少至二句为一个歌节,有多至六十八句为一歌节),但多数仍为四句一个歌节,例如《离骚》就是这种特点的代表。”而且,楚辞“歌节”“以双为单位”:“楚辞中的歌节多数以双为单位,除四句为一个歌节的基本形式外,还有六句、八句、十句、十二句、二十六句、五十四句、六十四句等。单句歌节也有,但少见,如《招魂》中就有七句、十一句为一个歌节的。”黄凤显先生也说:“四句一‘歌节’和以双数‘歌节’为主的特点,形成了屈辞‘歌节’中整齐匀称的节奏。而少于四句或多于四句的‘歌节’以及若干单数‘歌节’的使用,则体现了屈辞‘歌节’长短相错、偶奇交叉的节奏变化。”
关于楚辞“歌节”的性质和成因,学者们主要是从诗体文学的观念出发,侧重于从“意义”、“形象”的层面分析。譬如,对《离骚》的划分,朱熹《楚辞集注》首次划分四句一节,而“马茂元先生的《楚辞注释》和聂石樵先生的《楚辞新注》,都没有完全按四句一节划分,采用的是近似于‘意义层次’或‘意义单元’的分法”。这就把“歌节”看成“意义单位”了。黄凤显先生认为“歌节”的形成,是“意义形象”的需要,他说:“屈辞章节仍以四句一节最为常见。这种现象固由声律要求所致,却不便完全归结于声律。透过其语言符号,我们可以发现,四句中所构成的画面形象往往类似于电影中的一个‘分镜头’,而其所表征的意义情感也常常已经相对独立完整。四句中的意象已组合为一个‘小’意境。因此,四句一间歇,既是‘歌节’之要求,也是形象意义上的独立。其内在的制约,则是意境。如意境未成,歌节’必会加长;如意境已成而‘歌节’仍欲凑其四句之数,则不堪想象。”又:“屈辞的章节结构并不都墨守其声律规范,而以创造意境为要,以表达思想情感和意象组合为内在标准,然后以‘意’适‘声’,据其意境以合声律。”
然而,学者们又不能忽视“歌节”内部存在的声律回环自足的特点,于是认为既是“内容的要求”,也是“乐曲的要求”。如,麻守中先生说:“楚辞歌节的划分,一是内容的要求,二是乐曲的需要。”但是,他又分明感到楚辞“歌节”是“形式”要素,他在讲到“楚辞的曲式(章法结构)”时说:“歌节是楚辞曲式组成的最小单位。”“楚辞体诗的章法结构是和楚辞的曲式一致的,有鲜明的音乐特色。”但是,非常明确地指出“歌节”是楚辞的“形式”要素的是赵逵夫先生。他说:
四句为一节。也就是说,每两个作为诗体组成单位的“兮,”构成一节。这首先是由押韵表现出来的,押韵、换韵都是以节为单位。屈赋中也有两节以上同韵的,但必是以节为单位。屈赋中的节同《诗经》中的章是不同的……《诗经》中的章是据内容而划分的段落,并不是诗体形式上的固定的组成单位,因此,一章必是叙一层意思。屈赋的节却是诗体形式的一个因素,是外部结构的表现,因此,可能一节叙两层意思,也可能数节叙一层意思。王夫之《薑斋诗话》卷一说:“句绝而语不绝,韵变而意不变,此诗家必不容昧之几也。”王夫之正是看出了诗的句、韵是属于形式方面的因素,语、意是属于内容方面的因素。形式的变化应与内容尽可能相一致,但形式对内容并不起束缚、局限的作用。因之,作为诗体固定格式的诗节,不一定同抒情、状物、叙事的起讫变化相一致。
这段论述精辟深刻,可以整合“歌节”研究中的诸多歧见。但是,赵先生认为:“《离骚》是诵诗,不是唱诗,所以它完全脱离音乐成了独立的语言的艺术”,“屈原的作品,除《卜居》《渔父》及就民间祭祀歌舞词润色加工而成的《九歌》之外,都是‘诵诗’。”“屈原所用诗体形式当时谓之‘诵’,汉代谓之‘赋’……这两个名称,都反映了屈原所用诗的形式是脱离了音乐而独立存在的诵诗。”这就否定了楚辞的“乐”性特点,值得商榷。
造成上述观点分歧和自身矛盾的根本原因,是研究者用诗体文学的观念和理论来解读乐体文学作品。如果我们把楚辞放回乐事活动中,从乐体文学作品的角度去思考,就会发现,“歌节”是楚辞结构作品的最小的形式要素,它所体现的是乐歌“旋律完型”的要求。
关于“歌节”的“旋律完型”特征,可引用赵逵夫先生对《离骚》“歌节”分析的话来说明。赵先生说,《离骚》的“歌节”,“单句之末带泛声的语助词‘兮’,使上下两句成抑扬之势;同时,这个‘兮’字使上句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独立性,从而同下句语气上形成似连非连的关系”,“上句连接下句,其义方足。从内容表现上来说,由于上下两句语气的贯通,句子的容量增大,可以更有效地表现曲折复杂的内容;从结构上说,一章诗便不只是若干六言句的联结,而成了若干个‘兮,’的联结。上句末尾带‘兮’,读起来余音摇曳而语调较低、较轻;下句末尾不带‘兮’,而有韵脚,至句尾声音拖长,语调较强。这样就形成更为明显的抑扬之势,造成更为强烈的节奏感”。在此基础上,我的补充是:一章诗“不只是若干六言句的联结”,也不只是“若干个‘兮,’的联结”,而是若干个“歌节”,即“兮,兮,”的联结,这种联结形成基本的旋律自足的单位,即最小的“旋律完型”,如此,方能形成“‘弱—强、弱—强’这样回环变化”的旋律美。这种基本的“旋律完型”,是基于宇宙的生命节律和人对这种节律的生命体验及其心理追求的。
正是由于这种“旋律完型”的要求,使得每个“歌节”中的“意义”和“形象”有了相对的“完型”,犹如学者所说:“四句中所构成的画面形象往往类似于电影中的一个‘分镜头’,而其所表征的意义情感也常常已经相对独立完整。四句中的意象已组合为一个‘小’意境。”因此,我们认为“旋律完型”要求“意义完型”、“形象完型”,这是“歌节”产生的内在的、真正的原因。
《楚辞》中每篇作品就是由许多这样的“旋律完型”(自然也有意义和形象)的“歌节”构成的,正是由于这些“歌节”的前后连属推进,构成了回环往复、波连涡旋、后浪推前浪、连绵不绝的更大的旋律,也正是因为这些旋律的波涌涛连,起伏回旋,自然而然地“带出”——而不是“写作”——了细深婉曲的叙事和抒情、诘问和呼招,“带出”了鸿富、巨丽、奇谲、宏深的篇体结构。因此,我们说,四句一节、双数为主的基本的“旋律完型”——“歌节”,是楚辞文体曲式构成的最小单位,也是楚辞作品产生的“秘密”所在。
总之,楚辞文体四句一节的基本的“歌节”形式,是“旋律完型”的体现,“这同诗的以内容转变为准则的段落划分是两回事,它完全是形式方面的问题”。它所体现的是楚辞作品受制于音乐——歌舞的节奏而形成的一种内在的旋律,这与《诗经》“二二——四”式受制于音乐——舞蹈的节奏相同,是“诗—乐—舞”的旋律的外在体现,是乐体文学作品的形式要素。
三、“乱”、“少歌”、“倡”:楚辞乐章结构的音乐处理手法
(一)“乱”、“少歌”、“倡”等音乐处理手法在《离骚》《九章》《招魂》的运用,是楚辞作为乐体文学作品在结构形式上的又一显著特征
1.关于“乱”
“乱”是终了的乐章。“乱者,乐之终也”,“合乐谓之乱”。朱熹《楚辞集注》:“乱者,乐节之名。”不仅如此,杨荫刘说:“‘乱’是有关音乐处理手法的一个专门名词。”
楚辞中标明“乱”辞的共有六首:《离骚》《招魂》《九章》中的《涉江》《哀郢》《抽思》和《怀沙》。“乱”,在周代乐舞《大武》和《诗经·关雎》中已有运用,只是《楚辞》中“乱”的运用更为灵活多样。如《离骚》中的“乱”辞只有四句,开头用“已矣乎!”的惊叹句引起;而《招魂》中的“乱”辞则有十四句,末尾以感叹句“魂兮归来,哀江南!”作结。这,“说明了当时的音乐创作艺术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乱’成为一个通用的专门名词”,且“在当时已得到相当普遍的承认、肯定和应用”。
关于“乱”乐的特征,王逸《离骚注》说:“发理词旨,总撮其要”,“结括一言,以明所趣之志”,这是着眼于内容。蒋骥《山带阁楚辞余论》说:“旧解乱为总理一赋之终,今案《离骚》二十五篇,乱’辞六见……余意‘乱’者盖乐之将终,众音毕会,而诗歌之节,亦与相赴,繁音促节,交错纷乱,故有是名耳。孔子曰:洋洋盈耳,大旨可见。”这才说到“乱”乐的特质。杨荫刘说:“‘乱’的内容可以多样:可以是华丽热情,如《关雎》;可以是雄壮、热烈和庄严、和平,如《大武》中间的两个乱;也可以是悲伤愤懑,如《离骚》,但其为高潮之所在则一。乱’在《离骚》中是对其前多个歌节的节奏形式的突然变更——这一突然变更,就以前诸歌节所已肯定而且在人的感觉上所已稳定下来的节奏而言,会起一定的‘扰乱’或对比作用,从而增强音乐上特别紧张的高潮效果……‘乱’一开头就用‘已矣乎’一句表示出无可奈何的绝望心情。这一句,在节奏上是外加的;在内容上,是要求有能够深深刻画内心绝望心情的音乐,不适宜于轻轻带过。作者在其后的一行中,用‘国无人’、‘莫我知兮’,由两逗构成、中间顿断的句逗形式来表示他对绝望环境的毫不游移的决然的论断。这在节奏和旋律上又要求应用不同于其前各节的表达手法。”
所以,“乱”不仅是乐章结构,也是音乐表达和处理的一种手法。这,却是我们所忽略的地方。如此,“乱”作为乐章结构和音乐处理手法,它在楚辞中的运用应当不限于上述六首,因为,《关雎》中虽无“乱”的标示,但孔子说:“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确信它是有“乱”乐部分的。依此,楚辞中凡可歌可舞的乐的尾声部分也应当是用“乱”乐来处理的,只是未作标示而已。
总之,“乱”是终了的乐章,是尾声。乐曲终了时一般要形成一段高潮,所谓“繁音促节,交错纷乱”;与之相应,乐之“乱”辞也要有概括总结全篇内容。由于“乱”乐在思想内容和音乐节奏上都要达到一篇作品的高潮,因此“乱”辞在表现形式上和前面的歌节有很大的不同。“首先,乱’辞一般比前面的各个歌节要长,长,便于发挥,有突现高潮的作用。其次,乱’辞和前面的各个歌节相比,在句法上都有突然的改变,说明在音乐上也必然有节奏的改变,这种节奏的改变也有突现高潮的作用”。第三,“‘乱’若是高潮所在,则除了结构的长短,节奏的变化以外,可能在旋律的运用,速度的处理,音色的安排,唱奏者表达手法的运用等方面,都会有其突出之处”。
2.关于“少歌”和“倡”
“少歌”和“倡”,与“乱”同时出现在《抽思》中。王逸注“少歌”:“小唫讴谣以乐志也。少一作小。”注“倡”:“起倡发声,造新曲也。”又注《大招》“讴和《扬阿》,赵箫倡只”曰:“先歌为倡,言乐人将歌,徐且讴吟,扬举善曲,乃俱相和,又使赵人吹箫先倡,五声乃发也。”
现代学者研究认为,“‘少歌’可能是歌曲演唱中的小的高潮部分。倡’可能是不同曲调连接时插入的过渡性乐句。少歌’与‘倡’都是‘楚声’在艺术形式方面出现的新因素”。“‘乱’可能具有进入高潮和结束乐曲的作用;‘少歌’和‘倡’据近人推断,可能具有小结、间奏、过门等作用……可以推想那时既然用了这么多不同的处理方法,它的表演规模和给人们的艺术感染力一定是很大的”。还是杨荫浏先生的分析客观深透,他说《抽思》乐章结构:“1.在一个曲调重复了十次之后;2.用一个‘少歌’作小结;3.之后,用‘倡’引起后面的曲调(同一曲调或另一曲调);4.在这个曲调五次重复之后,5.在末尾用乱作总结。这里,少歌’和‘乱’同样是结束的段落;所不同的,似乎是:在一个需要用到两个结束段落的较大型的曲式中,少歌’是前一小结性的小高峰之所在,乱’是最后总结性的大高峰之所在。这样说来,《抽思》中的‘少歌’和‘乱’其作用正相当于《大武》中间的两个‘乱’。两者名词虽异,实际相同。而‘倡’呢,则似乎是:在对前半曲作了小结,需要向下半曲过渡之时,中间插入的一个小小的过渡段落,其作用在更好地引起下半曲。”
和“乱”相同,“少歌”和“倡”既是一种乐章结构,也是一种音乐表达和处理的手法,那么,它在《抽思》以外的作品中也应有所运用,只是未标示而已。这只是一种合理的推拟,已难确证了。
(二)《九歌》“诗—乐—舞”三位一体的乐章形式,更接近乐体文学的原生形态
《九歌》中虽没有“乱”、“少歌”、“倡”等音乐处理手法的标示,但它那“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表演性,更接近乐体文学的原生形态。后人常把《九歌》改编成歌舞剧进行演习,便是明证。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八《相和歌辞三·楚辞钞》中就有“魏晋版”的《九歌》:
今有人,山之阿,被服薜荔带女萝。既含睇,又宜笑,子恋慕予善窈窕。乘赤豹,从文貍,辛夷车驾结桂旗。被石兰,带杜衡,折芳拔荃遗所思。处幽室,终不见,天路险艰独后来。表独立,山之上,云何容容而在下。杳冥冥,羌昼晦,东风飘飖神灵雨。风瑟瑟,木椱椱,思念公子徒以忧。
朱谦之先生说:“究竟魏、晉乐所奏,是不是《楚辞》本来的唱法,或者魏、晋时楚汉遗声还没失传,也许就是本来唱法,也未可知。而《楚辞》之可歌唱,且曾用歌唱过,也是一个确实的证明了。”
上世纪四十年代,闻一多先生写了《〈九歌〉古歌舞剧悬解》,八十年代,李大明先生受此启发,编写了《〈九歌〉歌舞剧新编》,力求恢复《九歌》“诗—乐—舞”三位一体综合艺术的“原貌”,这是有益的尝试。还有学者从《东皇太一》“扬枹(鼓槌)兮拊鼓,陈竽瑟兮浩倡”和《东君》“缏瑟兮交鼓,箫钟兮瑶簴,鸣篪兮吹竽”的句子中,推拟“《九歌》的伴奏乐队可能是以编钟和建鼓为主要乐器,并附以竽、篪、瑟等管弦乐器。这种乐队就是所谓的‘钟鼓之乐’”。
结论:我们认为,《楚辞》是南楚神巫文化土壤中孕育生成、在乐事活动中或舞歌、或诵歌、或招歌、或问歌、或讲唱的乐体文学作品,它并非后世意义的诗体文学作品。它的语句形式:“兮”字句;曲式构成的基本的单位——四句“歌节”;乐章结构的音乐处理手法:“乱”、“少歌”、“倡”等;足以证明它是一部乐体文学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