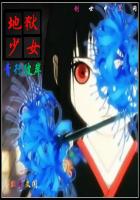刘澜说:“喂,你可别把我当第三者,邱局追我追得苦,说实话,只要我答应,他随时离,随时同我结,就这么简单。这对你也许是个打击,我结的人是你的下属,圈子里传出去不好听,可我也是没法,你想,如果我嫁个擦皮鞋的,你会更不好受吧?”
杨大吉说:“我无所谓,我是为蔡月牙的事儿来的,你得给她个交代。”
刘澜说:“怎么交代?邱局长也还欣赏她,这也可能成为我的脱壳之计,不需要脱壳了,你还叫我让?”
刘澜不仅是直爽,也许还带着某种挫伤,对手当然是他杨大吉。杨大吉不会在乎这个:“你想错了,月牙也许不一定像你想的找个局长往上跳,可是她必须调出来。”
“还调县里来?”她的疑问里有自挖墙脚的意味。
“调市里。”
“调市里?从村里调市里?异想天开吧。”
杨大吉说:“我可不管这么多,你多做好事,必须做。”
刘澜说:“哟,为啥?”
杨大吉说:“和我沾上边就得这样。”
刘澜说:“我没和你结婚。”
杨大吉说:“你能否认和我有关系?多做善事,也许能逃掉什么!”
刘澜不吱声,此时在她眼里,杨大吉不是个魔鬼,倒是个巫师。
杨大吉说:“也许呀,你这一赌气,都是一种预言,说不定邱局长有艾滋,这下你是上了贼船了。”
刘澜骂了起来:“你是变态,谁赌气了?我就喜欢姓邱的。”
杨大吉明白,自己的火气不仅仅是为了蔡月牙,自己为什么就是别人沾不得边的人呢?
马依莲失踪几天,到石头桥镇去了。她相信刘丁头的话,不易不是来兴的。她应该把那个人找到,把孩子交给那人,然后和杨大吉一起去面对那种无形的恐慌,那很惬意。
马依莲相信刘丁头的话,还有刘来兴的表现。刘来兴对不易痛在骨里,爱在心里,那时他常常掰着孩子的脸摸个不停,对她说:“孩子像你。”
马依莲打个冷战:“有些像我。”
刘来兴说:“不,全部像你。”
马依莲平静了些:“怎么,不希望他像你?”
刘来兴说:“是,我蠢。”
如今马依莲知道了,刘来兴也像自己一样,怕不易像别人,庆幸,孩子越来越酷似自己。刘来兴说:“孩子像娘,会有出息。”像娘什么也可以掩饰住了。可是那时他不知对马依莲是多大煎熬,她多么希望刘不易有些像刘来兴,哪怕是耳朵像也好,她不相信就是那次不幸的结晶,前前后后刘来兴都努力过的,应该是这样,应该是!
刘来兴出去时,总会把些事儿托付给刘丁头。他会对她说:“丁头你放心,是我兄弟。”之后,他必得冷酷一句:“如果他胡说八道,我会杀了他。”
她以为指的仅仅是调戏,还有别的呀,刘丁头什么都说了,不怕来兴杀了,他也以为他死了。
马依莲是带着孩子去的。刘不易问去干什么,马依莲说石头桥有人曾经去深圳打过工。刘不易以为还是去找爸爸,就问:“不是说爸爸没了吗?”马依莲不好说什么,她心中不易的“爸爸”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他们来到了一个村,叫泥头人村。据刘丁头讲,估摸离石头桥镇不远,向西一点点。那应该是这里了,隐约记得当时有个榨油的地方,荒弃之地,供人休憩。问了几个来回,知情的人讲,这么个地方是有过,早被拆了。
那么那个荒唐的地方彻底灰飞烟灭了。她开始想那个人,那个人也应该离这儿不远。刘丁头不知,只道应该是个聪明的种。从这点上,她有些感谢刘来兴,按理,他完全可以叫刘丁头帮忙的,但丈夫是个负责任的人。马依莲固执地以为应该是个老师,还应该是个初中的老师,她把目标锁定在石头桥中学。
石头桥中学也在镇西,放假了,很是寂静。她在校门口租了一间房子,观察来往的行人,好像是在做特务工作。
马依莲先入为主地刻画一个人。她记得那几天他们谁也没说一句话,不准说一句话。他们的脸是蒙着的,只留出气的地方,她甚至淫秽地想,她的手甚至没有接触那物件。她只是凭感觉。感觉?她不能不一一回忆那些镜头。她想,她是被强迫,他在呵斥。现在想来,那种呵斥有假装的成分,也是被逼的哩!呵斥之后她居然投入了。她觉得对方的一切是圆润的,应该保养得很好,也很文质彬彬。她以为他应该是个老师。他的长相呢?年纪应该和自己差不多,或者大点,应该大点,在那方面显得老到。不易真的一点都不像他?唉,她突然埋怨不易太像自己,要是露一点馅儿该多好。
马依莲想,如果真正找到他,她会爱上他的,她会认真听听他的委屈。他可能有个家吧?那是肯定的。那么她怎么能爱别人呢?她越来越觉得自己的主动过了,还好,一切为了孩子,对,绝不是为了自己。
马依莲一无所获。这也许是最理想的答案。住的房东听说她是六角坪的,问:“认得你们镇的杨县长吗?”马依莲不好说什么。房东说:“他到这里当过书记,老百姓很记挂,可惜被一个女人害了。”马依莲引起警觉:“哪个女人?”房东惊讶:“你不知,你不是六角坪的吧?”马依莲说:“真是六角坪的,只是少闻得很。”房东缺乏了交流的激情:“我也不知具体的,传的是个农村妇女,她男的是痴呆。”马依莲哭笑不得,连忙清东西,说是回家。房东问:“你不是带儿来假期补习的吗?”这里的学校挺有名,几个名师家教更有名。马依莲说:“算了,算了,跑到别的乡补还是少了脸。”
马依莲带着刘不易向车站而去,途经农贸市场,一行人在那儿参观,是县里的一批党委书记,蔡鸣也在。马依莲招呼一句,蔡鸣佯装未闻。刘不易也认识他,高喊蔡叔叔,蔡鸣没办法,才睬了。一些同行的人连忙打蔡鸣的趣,问是什么亲戚,蔡鸣也不多介绍,把马依莲拉到一边,叫她快带孩子走。马依莲好像做了什么错事似的,拔腿急行。刘不易问:“妈,蔡叔叔怎么没得以前和气?”马依莲说:“他很忙。”言语短促,拖得刘不易跟不上。
马依莲从石头桥回来,很想把事儿告诉杨大吉,而他却给蔡月牙办事儿去了。马依莲有点躁,应该把刘不易的秘密告诉他,不该隐瞒什么。等了两天还没来,她的情绪平息了许多,想来想去又改变了主意,还是以后再说吧,那毕竟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
杨大吉本来差不多可以同时回高就的,是蔡鸣带信,滞留在六角坪镇里了。蔡鸣当初并不主张他买山,没必要吃这个亏,真正当上了主儿,蔡鸣又不能不支持。蔡鸣说:“你组织一批竹子,有个大主要来。”这是他此次参观中获取的一个信息。杨大吉喜上眉梢,就一起喝了点什么。喝得上了劲,蔡鸣说话直了些,问和马依莲的情况。杨大吉装相:“没事儿呀。”
蔡鸣道:“别瞒了,县里传的不少。”杨大吉哦呀一声:“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蔡鸣接着问:“你也认为是坏事?”杨大吉道:“我还没有再婚的打算。”蔡鸣道:“我倒不这么认为,要结就正儿八经,那刘来兴登报了的呢?”“好像没有回音呀!”“问问法院,看失踪多久才再来得。”杨大吉笑道:“你是怕我名声不好。”他不认真入题,蔡鸣不好再说。杨大吉却又蹦出他想听的话来:“我问了陈苏道,他说下落不明要四年才能宣告死亡,才会有后话,而今哪个也不会想正经事嘛。”蔡鸣笑了笑:“苦呀,那千万别陷进去,还不知以后的事。”杨大吉也笑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