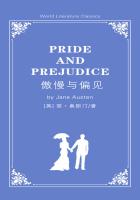杨大吉回了一趟县城,几天工夫,又回到老家。
县政府值班室通知,说是有重要事情请他回来。县里干部要调整,也牵涉到政府办,得听听他的意见。很多事儿只是一程序,没必要陷入一些是是非非,他想表示一种存在就行了。
他的办公室依然保留着,积满灰尘,搞服务的人扑进来说,前面天天打扫了的,最近才疏忽。他淡然一笑,为官多年,深知千万别为一些小事和小人物计较,受了些委屈,也得表些胸怀,否则降低了自己的层次。接着蔡鸣来道歉,杨大吉就不能表示无所谓了,多少应该给点刺激。蔡鸣却少给机会,象征性表露后,迅速转入了自我的张扬。他没把道歉当回事,那只是一个开场白。他又有什么道歉的呢?政府办本来忙,杨大吉又没来上班,何必多费精力亲问呢?连杨大吉也想,没什么的,可就是有些不快。蔡鸣没有觉察这些不快,而是告诉,跟张县长跑了这么久,在政府办要扶正了;说等工作调摆好了,再去看老领导,去高就村看看,那里他太熟悉了,不止一次跟随去过,去看杨白成,还问起高大妈:“她儿子应该找到了吧?”
杨大吉觉得他像是和一个老乡谈话,机械地应道:“没有,登报了,也没见什么效果。”
蔡鸣的兴趣却越来越浓,连杨大炮也扯了一会儿。
杨大吉对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才无谈兴,暗中揣度的是,自己离开了这么久,蔡鸣居然一点也不谈县政府和李上述的事情,怕挨边惹事吧。
接着,蔡鸣要接吃饭,杨大吉说无空,蔡鸣仗着以往的亲密,道:“还这么忙呀,我的饭你还是得吃。”
杨大吉没有回应,只问:“张县长不在?”
蔡鸣说:“到市里开会去了,不然他还会不来见你?”
这一下又生分了许多,蔡鸣的一言一行向着张满园了。杨大吉内心生冷时,江尧来了电话,亲热得一塌糊涂,说是以老乡的身份接吃饭。杨大吉连忙接应:“好哇,邻居嘛,不吃你的吃谁的?”
蔡鸣非常难堪,欲言又止。
杨大吉似乎考虑了蔡鸣的感受,感慨道:“怪不得,越是疏远的越要顾及,退下来也不值钱,该应酬的一个不落。”
“那是。”蔡鸣应话,前面的热情大幅下挫,有传江尧马上要转任财政局长,一些可能的反对势力尽量地套近乎,他料定杨大吉还不知。
江尧的接请在瑞云酒楼,还有刘澜在场,杨大吉略为意外。江尧自吹自擂的本性还在:“杨县长,这回我可帮了刘大记者一个大忙。”
“不错,拉了一个大广告。”刘澜挺上心的,在报社里面,记者都有任务的。
江尧接着说:“刘大记者说感谢,我说什么不要,只要请陪一餐饭。”
全是踌躇满志之状,杨大吉也不在意,道:“春风拂面了,那就让记者写条新闻,江大局长如何密切联系群众。”他不明白怎么跟着也油腔滑调起来,而且还自轻自贱。
江尧说:“岂敢岂敢,我是怕没得面子,还好,没把大记者抬出来,你就答应了,谢谢,谢谢。”
刘澜端起酒杯,豪言:“没想到我在人们心目中,能在杨县长面前有些薄面,惭愧惭愧,我先干为敬。”说完,爽利地一口吞了下去。随后,她居然站到江尧一边,接二连三地发起攻击,让杨大吉一顿酒喝得够戗。八九不离十了,刘澜应酬了几句,公事公办地又一阵风先走了,说是赶回市里有啥事儿。
江尧开玩笑道:“杨县长,莫非刘大记者有什么新情况?”
杨大吉道:“那是她的事儿。”
刘澜一走,江尧有些话说敞亮了些:“对不住,过去有些不周的地方得多包涵。”
杨大吉表示理解:“哪里话,各有各的难处。”
江尧连连致谢,好像一餐饭别人请的,又表明决心,将来有啥事儿,只管说,一切照办。
杨大吉便感到了无聊,一种虚情假意的无聊,他欣然地接受吃请多少是对蔡鸣的一种古怪回应,而受伤的还是自己。
他感到和过去的某种隔膜,包括和自己他都感到了陌生,比方有人传说当初他犯市领导的臭话是江尧传出去的,他见小人怎么能这般从容呢?至少也不该为伍呀?然而他却这么随意地火热在一起了。也许退下来后,许多恩怨也没了界限,硬气、志气随之消退,台上台下区别真这么大吗?
他不想更多地碰到熟人,知趣则罢,不懂味的问起李上述的事,他会难于应付。他把自己困在屋里。这个称之为“家”的地方,隔膜似乎更久了。杨妮的房很久没进去,多了些恐怖;进卧室又想起李小蓉,离开前的一段日子,他们分了居。他这回仍旧住书房,这里相对多些生气。他一直不明白的是,刘澜怎么了?李小蓉在时,她经常提出要到他屋里来,只来一次也行,他无法答应。而此次到了大昌,她怎么又匆匆返回市里了呢?是真有事忙吗?抑或又远离自己了呢?而这,不正是他期待的结果吗?
房子还是得弄生气点,请来一个清洁工,五十元一天。清洁工从卧房的床底下,扯出一摞报纸,意外的是那上面差不多都有刘澜的文章,这是又一个像蔡鸣一样的有心人!他确信是李小蓉读了的,最早的到了一九九九年,也就是他和刘澜相好的第二年!第二年?第二年!杨大吉惊叹了!李小蓉是一个多么经得住煎熬的人!一屋的人都以为她听到传闻只是近年的事,她更会伪装,她把所有的人骗了,包括母亲,要不,老人怎么会邀她去旅游解解愁呢?唉,这就是某种宿命。要是她是一个吵吵闹闹的人呢?也许后面的许多故事就没了。他再仔细翻了翻,她还在上面画了一些杠杠,打了一些圈圈,写了一些评语。他太了解李小蓉了,她是试图通过文章了解刘澜这个人,了解自己缺乏的是什么。
杨大吉不知如何处理这些报纸,把它转给刘澜,已无必要;那么,带回高就村,来年清明上坟上去烧呢?矫情了,越想越感到一切怀念和愧意都是多么苍白!
几天后,杨大吉接到蔡鸣的电话,心里暖和了许多。蔡鸣说是到医院看望病人时,碰到高大妈在那里诊病,还念叨杨县长!蔡鸣说:“她说一声想你,我好激动,也给了两百元钱。”看似有点做作,也让杨大吉揪心。他问:“你说李上述还能出来吗?”蔡鸣语调悲切:“不知,前景未卜。”杨大吉说:“唉,我不下台,也许不会有事。你说,这是不是对我来的呢?”蔡鸣说:“你多想了,这都是外面瞎猜,他还是过去狂了点,只是没你罩着了,差是差了些。”杨大吉叹了一声,说:“有机会再出来,你一定接他吃饭,不管我在哪里,都来陪。”蔡鸣哽咽:“好。”
也就是蔡鸣的那一提醒,杨大吉看望了高大妈,然后,一起回了高就村。
蔡月牙没想到杨大吉这么快回来,她说:“我还准备给你打电话呢!”
杨大吉的语气生硬:“有事吗?”
蔡月牙说:“没事,只是以为你暂时不会回来。”
杨大吉的嘴巴咂了咂,自己也以为暂时不会回来,他会把村里的这个家当“家”吗?说不好了,但至少不想这么快见到蔡月牙,当初那么急促离开高就村,政府办催是回事,从内心里这也是个理由。他想起高大妈说的两升米来了,他不能像父亲那么做,他也无后人还账了,问:“说吧,我能为你做什么?”
蔡月牙说:“你误会了,没事,将来也不会有事。”
杨大吉将信将疑。蔡月牙说:“我那天的那个是一时的冲动。”她踢了踢脚,显然是不愿意这么说出来的。
杨大吉的血往上涌。是自己小家子气了,他以为应该有什么事的,比方以前耿耿于怀的安排工作的问题。如果真的什么也不做,他心里又有些缺失,疑心失了误,少了些麻烦,又多了些伤悲。
蔡月牙却说:“有人的事你却不能不管。”
“谁的?”
“刘姐的,你可欠人家的情。”
杨大吉用审视的眼光望着她,不知这女孩到底知多少,自身的虚空在不断加剧。
蔡月牙知道得够多的了,杨大吉离开村子的几天,正好过元旦节,蔡月牙也去了市里,到了刘澜那儿。刘澜出奇的热情,她们一起吃睡,一起逛商场,一起泡茶馆,简直快乐无比。蔡月牙不明白这样让人着迷的女人仍旧单身。刘澜说了自己的故事,她和杨大吉的故事。蔡月牙听得非常憋气,他们的关系好不必说,没想到会是这样,还这么长久。有些兴奋的是,刘澜居然对她那么信任,那样一览无余,从了解内情来看,她可能起步较晚,却最先到达终点。
杨大吉实在没有好多说的,他也明白刘澜的意思,他们的情感一抖出来,可能的有心人也就望而止步了,也好,无形困扰的问题——蔡月牙的问题一下解决了。刘澜曾说,她是个有心计的姑娘,其实蔡月牙还是该归为单纯一类。
蔡月牙表现出一种高度的善解人意:“也不一下为难你,对了,有人接你吃饭。”
“是谁?”杨大吉问。
“是我。”高碧海也来了。
高碧海诚心诚意,理由是吴大妈过生日,除蔡月牙外,就接他一个人。杨大吉想到一些事儿,有点不自在:“是不是多个人凑合好些?”
高碧海说:“你是说村长吧,我不想接他。”
杨大吉说:“怎么接不得?”
高碧海说:“这村里就咱三个文化人。”
杨大吉笑了,笑他穷酸,待在乡里,还谈什么文化呀?
高碧海的住处多了一部电脑,在村子里多少算个新鲜事物。高碧海解释说元旦节回市里了的,杨大吉对蔡月牙一撇,她的脸就红了。饭局没开始,杨大吉上网玩玩,一打开桌面,发觉高碧海在炒股,问怎么样,高碧海说玩玩而已,也不在行。
吃罢饭,蔡月牙和杨大吉一起出门,忙着说明去鼎州的事:“一路去的,却并没待在一起,我待在刘姐家。”杨大吉说:“何必解释呢?”蔡月牙说:“不信就算了。”两人就分了手。看他们分手的是马依莲,她心里咯噔一下,把疑惑深深地埋着,说是来感激杨大吉的,来去搭帮他搞的车。
杨大吉搓了搓手,顺应也客气了一句。
马依莲又说:“婆婆好多了,我还是可以帮你收拾的。”
好个啥,还是瘫在床上,只是高大妈的脾气好了些,折腾一长,也得听天由命。到县城住了半个月,老人家只感觉一条,欠了杨大吉一万多块钱,效果并不明显。关于那钱,杨白成还怪杨大吉:“说好不是借我的吗?怎么真你借了?”杨大吉当然不会解释高大妈带来的变故:“还不都一样。”杨白成没好气地说:“横竖你的钱也没用。”杨大吉臭骂了他一句。高大妈觉得杨大吉这人好得不得了,逢人便说:“真不愧是当了县长的。”杨大吉其实并不想让更多人知情的,又不怎么好封口。
马依莲提出帮忙太快,杨大吉的心情复杂,好像帮了人家一点小事,就应该要回报,他拒绝了。
马依莲透些迷茫地问:“是不是只月牙就行了?”这句话自然还有潜台词,是不是烦她之类。
杨大吉说:“她也不用,我能行,再别把我当什么县长了,我给白成讲过,不用管我什么了,等几年,我只是个糟老头子,你们管得了些许呢?”说到最后一句,他心里也咯噔了一下。
马依莲说:“你说什么呀,看起来比我还年轻得多。”接着又打自己的折扣,“只是我显老呗。”
杨大吉笑笑,这女人心细,难怪杨白成有些想法。
马依莲心里好像堵了什么,还是接着前面的话:“是不是我出去了,月牙弄出了什么差错?”
杨大吉像受了什么敲打:“再别说了,这件事到此为止吧。”
马依莲不说了。可是她又想,他和蔡月牙刚才干啥分手的呢?应该没有什么误会,也许是他的真实想法。
马依莲给杨白成进行了汇报,这是大事,应该汇报。杨白成听后热情并不高,道:“行,不要收拾也行,也许他是怕什么闲话吧?”
马依莲不解地问:“那会有啥闲话?”
杨白成鼓了鼓眼睛:“要是人家说官退下来了,还那么显摆,你说他听得进去呗?”
马依莲说也是。
杨白成关心的还是她服侍高大妈在县里诊病的事儿,问:“刘丁头没对你怎么样吧?”
马依莲没吱声。
杨白成说:“你可防着点。”
马依莲还是未吱声。
杨白成说:“我这也是多余。”
马依莲终究不回声。
杨白成说:“也许你想防着的不是他吧。”
说完他们就散了。他们是在村部的门口散的,而又有一双眼从头到尾盯着他们,便是村长的老婆。村长的老婆也只是做做样子,什么也没盯着,天黑一会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