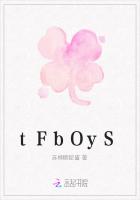后来的几天中,在同一地点,他们还在议论这个“天安门事件”,热情始终不减,还在某一天变得更加高涨和热烈——正是在这一天,我从他们口中,听到了干妈的名字和一个令我大吃一惊深觉恐怖的消息:干妈被公安人员抓走了!就在大白天在单位上被戴上手铐抓走的,罪名是在清明前后,私自参与了在本市新城广场所发生的同样以悼念总理为名的反革命煽动,她写了一首悼念总理的诗,并在诗后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和单位,在各地举行的同类活动被上面定了性之后,公安人员轻而易举就找到了她……
干妈被抓,似乎让窗子外头的这些长舌妇们感到十分的惬意和亢奋——
“叫她张狂!看她这下到号子里头还张狂不张狂了!”马天翔他妈说。
“这狐狸精平时见咱们女的老抬头挺胸的,根本就没把咱往眼里搁,见了男的那个骚劲啊!不瞒你们说:她在我们家老刁手下工作,我可是一直不放心哪!”刁卫国他妈说。
“还写诗呢?诗这东西能随便乱写吗?写不好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喽!真是连最起码的一点政治素质和觉悟都没有!”冯红军他妈说。
……
这件“大事”出了之后,学校的操场上很快便召开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誓师大会,各年级都指定有学生代表上台发言,三年级的代表是“小黄帅”习小羊,二年级的代表是我班班长刁卫国——我们院里有人才啊!
会开完了,和以往运动来时一样,学校要求:各班都要利用教室后面的黑板报办出一期大批判专栏来,还要进行全校性的大检查、大评比。
在我们班上,这项工作是该由宣传委员陈晓洁来负责的,苏老太太任命她做宣传委员,主要是看重她在文艺表演这方面的宣传才能,忘了把办黑版报这件事情考虑进去。陈晓洁虽然并不擅长于办黑板报,但搁在平时她一个人还是应付得了的,只是因为这一期的专栏要拿出去参加比赛,她便有点底虚了:她对她的字还是有信心的,主要是不满意自己的画,于是便心生一计想到我。其实在这时,她还没有亲身领教过我画得有多好呢,只是在我暗自学画以后,我在校内的美术课上已是今非昔比,画出的作业就有点鹤立鸡群的意思了,每堂课几乎都要受到老师的提名表扬,她听多了便留下了我擅长画画的印象。一天下午,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她向我提出:希望我能够帮她来办这一期的黑板报——也就是拿出去参加比赛的“大批判专栏”,当时我故做矜持了一小下,还是表示同意了——我有什么理由拒绝这个一向待我不薄的“小美人”的请求呢?
刚巧第二天下午正是我去南郊的美术学院学画的时间,等老师给我上完课,我向他提出了一个额外的问题:即黑板报——大批判专栏如何画的问题,他在大概了解了我的意图和需要之后说:“这个嘛,最容易。”他从抽屉里拿出了一本专门指导大家办黑板报和壁报的小册子,说这是他本人也参与撰写并绘制的一本书,让我自己读了然后照着上面说的来做。
有专家在背后撑腰,我的腰板挺得更直了。
于是在两天以后,便有了那么一个美好的下午,下课之后同学们全都走光了,我和陈晓洁留下来对付那块并不算小的黑板。
老师给我的那本小册子我已经在家仔细钻研了两天,我按照上头的一个示范图例,做了整体设计:有一个通栏的大标题,我用刚刚学会的美术字写道:“将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进行到底”(套用的是“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个范例)!然后在整个黑板的正中位置画了一个大报头,也是照着小册子中的图例画的:工农兵站一起挥手指方向那种的,在他们三人的身前还画了一名戴红领巾的女红小兵——这可是我自个儿想出来的:是照着陈晓洁的小模样画的——我画得有点像,她自己愣是没有看出来,这一方面说明我画画的功夫还不到家,另一方面说明人其实是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的——美人也不知道自己长得有多美的。等陈晓洁把所有的文字都抄写完毕,我又在边边角角的地方画了一些小图饰。在最后一块空白处,用圆形的篆书写了六个字:二年级二班宣——这一手,是两年前从干妈那儿偷着学来的,现在终于派上了用场——我在用鲜红的粉笔写完这几个字时,心情暗淡地想起了我的干妈:她怎么就给公安人员抓起来了呢?我接受的教育是:凡被公安人员抓起来的人都是坏人,而我的干妈怎么也不像是一个坏人啊!这是我无法想通的一件事!一想到此,我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很坏,以至于陈晓洁面对办成的黑板报像只小鸟似的跳起来欢呼时,我竟恍恍惚惚地没有太在意……
天已经黑下来了,陈晓洁锁好教室的门我们就离开了学校。走出学校大门,由于搬了家,如今该是朝西走了——从学校到现在住的家属院的距离和原来住的单位差不多,但方向却截然相反,还要左拐右拐地穿越两三条小街小巷,一路上陈晓洁还在兴奋不已地谈论着我们联手办的黑板报,穿过最后那条窄而长的没有路灯的黑乎乎的小巷时,她的手来抓我的手,她的小手很凉,像只受到了惊吓的小耗子似的,直朝我的手心里钻,那一刻,我全身上下的毛孔全都张开了,这春夜里头任何一点微小的风儿都会令我敏感,因为带着她的天然的体香,我的胸中也像是揣进了一只兔子似的……陈晓洁知道我回家是需要自己做饭吃的,就拉我到她家去吃饭,她家到底不是卢师傅家,在我看来,她的父母也不像卢福根的爹妈那般随和,我就说我不去了,走进家属院的门楼后,我们就分手了,她家住在二排,是住在习小羊家的隔壁……
第二天早晨,和往常一样,我是和卢福根一路去学校的,到得也比别人晚点,发现教室里头已经变得十分热闹了,所有先到的同学都在朝着教室的后墙看——欣赏着新鲜出炉的黑板报,相互打听着这是谁画的,有些人以为是陈晓洁本人画的,有些人说:报头上那个女红小兵画得像陈晓洁——这充分说明了我的绘画潜质,这三个月的画确实没有白学……我很得意又很矜持地坐下了,装得跟我没关系似的。早操的铃声响了,我们都先跑到操场上去集合做早操。等做完早操回到教室上早自习时,到校之后直奔操场的苏老师这才在这一天里头一回走进教室,她一眼便看见了后墙上的黑板报——那头一眼中甚至是带有几分欣喜的点点光亮的,怔怔地望了好半天之后,表情遂变得古怪起来,甚至充满了狐疑——就算我的想象力再丰富,预判能力再强,也无法想出她在这件众人都以为好的事情上的特立独行的反应——这位老太太终于结束了那长久的凝望与审视,快步走下讲台,几步就走到后面的黑板报前,回转身来厉声喝问道:
“这是谁画的?!陈晓洁——我问你呢!”
“是是是……我请……请武文革……画的。”
可怜的平时伶牙俐齿的陈晓洁被这突如其来的发问吓得给结巴了。
卢福根则忍不住地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只见苏老太太伸出她那瘦骨嶙峋青筋暴露的“鸡瓜子”点戳着“工农兵”中那个女农民高耸鼓胀的大胸脯说:“武文革!你这孩子!你脑子里头整天想啥呢!你这画的都是啥嘛?啥嘛?!你把人家农民的奶子画这么大干什么?人家又不给娃喂奶!是你想吃奶了是不是?是不是?!”说完,还用她那“瓜子”在大奶上一抹,一下给抹花了……
全班同学哄堂大笑。
卢福根等几个捣蛋的家伙简直笑得死去活来。
我一言不发地低头坐着,眼前的这个“错误”倒是没让我觉着太冤:我是把那个女农民的胸脯给画得有点大了——比书中图例上的要大。我也确实是有意画大的,我这是遵照我的美术老师的教诲从生活出发的,这是我内心深处不可告人的秘密:我是照着我平时观察过的并且牢牢地嵌在印象中的冯红军他妈的胸脯(作为原型)画的——那个胸脯是我到目前为止见过的女人中最大的一个胸脯!也是我认为最好的一个胸脯!它强烈地吸引着我!我就是有着把它画下来的冲动,就像是想把陈晓洁俊俏的小脸蛋画下来一样!
结果是:我没有按照苏老太太的要求把那个女农民修改成瘪奶平胸,陈晓洁也不敢擅自乱改。这块被苏老太太的“鸡爪子”抹花了一小块(她简直像是“阶级敌人地主婆”在故意搞破坏)的我们班的黑板报,还是在全校的大检查和大评比中脱颖而出,和高年级的某个班一起获得了一等奖。
我在美术方面的这点小能耐于是就被上头注意到了,我们的女校长还亲自跑到班上来,公开表扬了我一下,还跟我谈了一阵儿话,说要把我抽调去画红小兵大队部的黑板报——那是一块更大的黑板,是在老师办公室那排平房侧面的墙上,从学校大门口一走进来就能看到它,于是我就去了,在那么一个公开的场合画画,真像是在当众表演。而最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在自己班上并不负责黑板报这档子事,我连一名普通的红小兵都不是(又发展了一批还是没有我),但却画着红小兵大队部的黑板报。
由于有运动来了,“大事”发生——老在批邓老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个学期过得非常之快,一转眼就到了期末开家长会的这一天——这天上午我们学生还到了校,参加了在学校大操场上举行的学期总结大会,会刚结束,我就被兼管红小兵大队部的那名工宣队代表给叫去了,还是画那块大黑板,画上欢迎各位家长来校指导工作的内容,还要赶在两点钟家长们到来之前画完。领受了这项“紧急任务”,我马上开始动手,我之所以对这项工作怀有较高的热情,一是本来就爱画;二是爱在人前出风头;三是对于因此得到的来自学校方面的少有的肯定很懂得珍惜;四是让我在无形之中获得了一种面对苏老太太的傲慢——我确实需要这种感觉!
整个中午我都在那里写写画画的,到了吃午饭的时间,那个工宣队代表还从学校的教工食堂打来了两份饭菜,拉我到老师办公室里和他共进午餐——这也算是这一天的这项工作给我带来的一点物质报偿吧:省了我自做的一顿午饭。这个懒鬼,吃完之后他还让我帮他跑了一趟腿,去学校大门外头的一家百货商店给他买了两毛五分钱一盒的大雁塔牌香烟,然后接着再画,在此之后,女校长也跑来“关怀”了一下,“指示”我要抓紧时间,按时完成。本来我是可以赶在两点之前画完的,但是在一点来钟,一些热情过度的家长就提前赶来了,一走进学校大门就看到这块大黑板,便直奔此处,都站在我身后看我写字画画,其中就有我们地质队的这些家长——由于刘虎子和蔡铃莉的爹分别是单位里的第一、二把手,刁卫国的爹又是要管很多具体事务的办公室主任,所以单位专门派了一辆车把要到小学开家长会的人一起送来了。由于我爹人在野外未归,可以代他前来的干妈又被抓走了,所以将不会有人来给我开这个家长会,这让我感到心中特别踏实,甚至还有几分窃喜!
我面对黑板继续画着,但身后已难得清静——
“索索,吃了没有?”卢师傅最先开口问我——他是我们院子里头最关心我吃饭问题的人了,还老让卢福根喊我去他家吃饭或干脆给我送饭到家,有好几次我已经把饭做好了,他的饭又送到了……
“吃过了,卢伯伯。”我很认真地回答他说,“我们老师在学校食堂买给我吃的。”
“索索,今天晚饭别自己做了,到阿姨家去吃吧,我们晓洁可盼着你去呢!”陈晓洁她妈这个大美人也走上前来关心我。
我“唔”了一声——但我知道我是不会去的。
“这娃画得好啊!”刘虎子他爹这名“老红军”嚷嚷起来。
“画得好!画得好!” 蔡铃莉他爹这名“志愿军”也连声称赞。
“别看索索捣,这孩子是个人才!”卢师傅说——听起来更像是在替他儿子卢福根辩解。
“索索这画学得很有效果,看来你爸让你去学画是对的。”陈晓洁她妈评论道。
我面朝黑板,动作加快地画着最后的几笔,我看不到在我身后的场景之中,有那么四个大人被这料想不到的场景搞得很郁闷,他们分别是:习小羊的爹、刁卫国、马天翔、冯红军的妈——我甚至已经嗅到了习小羊他爹那一身的骚狐狸味(挺难闻的),还有冯红军他妈一身雪花膏的香气(挺好闻的),但却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在我画完最后一笔并且颇有点潇洒之意地随手扔掉手中的粉笔头时,还是听到了——是冯红军他妈这位大学老师、这位其他家长眼中最懂教育的“内行”忽然说出了意味深长的一句:
“认识一个孩子关键是要看穿其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