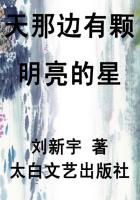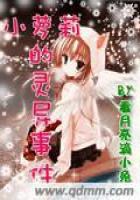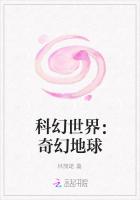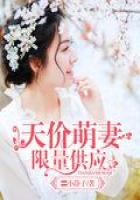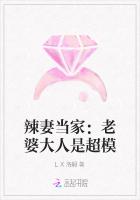我们素常总说,事业的成败与人心向背有关,但究竟怎样与民众有关,却很缥缈不定。在整个社会的大格局中,草民百姓,最属无权无势,一生老老实实为人,辛辛苦苦谋生,不招谁,不惹谁,还要忍受兵燹之灾、自然之害。这样的人,对当权者持何种看法,似乎都无足轻重,与朝廷的大事业更难沾边。这也正是一些人轻视、忽视这些小民的原因。项羽入咸阳城,见人杀人,看到宫殿就烧,《史记》说“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如此作为,百姓的感受,可想而知。在兵荒马乱年月,最能体现人心向背的自然不可能是参政、议政什么的,而只能是在偶然的行为中表现感情的好恶,比如田父对项羽的询问敷衍、漫应,促其陷入绝境,等等。
这类行动,都不是事前设计好了的,而是事到临头的现场发挥,十足体现了平日的思想。项羽兴旺的那些时候,不是杀就是砍,有一次要把降城15岁以上的男子全部坑杀,经别人劝说才放过了这些人。自始至终,他从没给老百姓办过一件好事,他的楚军给人心里带来的只是恐慌、绝望,而不是安定。在人心惶惶的氛围下度日,那叫“苟安”、“偷生”,人和一根草没有区别。田父“绐”这位西楚霸王,在心灵深处是有凭据的。
我不厌其烦地叙述田父的举动,并不是说项羽的悲剧全由这个无名者造成,只是觉得小百姓的态度应该引起人们深思。它最少说明项羽带给普通民众的,是恶劣的生存环境,小民从心底感到不满。这不免使人想到刘邦入关后的约法三章,今日看来条文内容没有奇特之处,不过杀人偿命那一套。可在兵火不断,视人如草芥的年代,这几条不啻百姓的救命草,人们“唯恐沛公不为秦王”是必然的感情。从政治策略方面而言,项羽杀人放火的举动,无异于弃百姓以资敌手。什么是政治?梁漱溟先生说:“所谓政治,不出乎保障私人利益图谋公共福利。”在某些方面,项羽可能要远胜于刘邦,但他轻视人的生命和福利,动辄放火杀人,民众对这样的人,从感情上不会认可。司马迁总结说,项羽“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项羽自己反而认为“天亡我”,可谓至死也没把百姓看在眼里,更没有把自身的失败与平时的所作所为联系起来。
原载《北海晚报》2008年9月5日
朱元璋“删孟”
黄 波
明太祖朱元璋“删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意味深长的事件。
作为亚圣,孟子的火气很旺,思想中也颇有一些原始民主主义的元素,他并非无原则地强调臣民对君王的服从,相反还认为,恶法非法,暴君非君,面对恶法和暴君,人民有反抗的权利。“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些都是中国思想史上光彩夺目的名言。历代的帝王,面对这些话不可能多么舒坦,不过他们更愿意装聋作哑,因为你孟子宣扬的是暴君非君,而我是明君圣主啊,何必和这些话过不去?
然而,朱元璋却不干了。他读《孟子》,到“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那一段的时候,不禁暴怒:这哪里是臣民能够说的话?皇帝一发怒后果就严重了,居然要罢免孟子千百年来在孔庙里和列位大儒们吃冷猪肉的资格,而且特地下令,不准臣下对此发表反对意见,否则就要处以“大不敬”的罪名,杀头。可偏偏也有不怕死的读书人,一个叫钱唐的士子还是毅然上疏,反对皇帝把亚圣打入冷宫,且公开声明说:“我为亚圣而死,虽死犹荣。”朱元璋这个时候总算冷静了一些,没有处罚钱唐,不久也恢复了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不过终究余恨未消,于是命令臣下“删孟”,将上述那些光彩夺目的名言尽皆删去,共砍掉孟子原文85条,只剩下100多条,编就了一本《孟子节文》,又专门规定,科举考试不得以被删的条文命题。
朱元璋为什么“删孟”?“删孟”背后的心理是什么?
在我看来,朱元璋对孟子强烈不满,和其“删孟”的举动,正是他竭力建立一种“新道统”的标志。
读中国历史,当代人常会奇怪,传统社会“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君王淫威之下,那时的人们肯定是极度缺乏尊严,天天垂头丧气的,特别是在自尊方面比较敏感的文人,但事实是,旧时代的士子们似乎并不觉得自己活得有多么窝囊,哪怕要直接面对高高在上的君王,他们也并非总是那么一副谦卑可怜的贱相,自认为该争的也还是要争个不亦乐乎,甚至常常至死方休。更令人诧异的是,这些“藐视”君权的狂人,虽然难免结局凄凉,有的要被打屁股,有的会被杀戮,甚至遭遇灭门灭族之祸,但民间的清议,也就是今日所说的“社会舆论”,还是公然站在他们一边。被君权打压甚至消灭了其肉体的,虽败犹荣,虽死犹荣。即便是要啥有啥的皇帝,对这样一种状况,也好像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之所以有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因为中国的读书人死扭着“一根筋”:他们倔强地认为,代表世俗权力的“治统”在皇帝那儿,而代表意识形态的“道统”却在我们手里。
这种“治统”和“道统”分割的现状让朱元璋愤怒,他雄心勃勃,要将“治统”和“道统”合二为一。朱元璋“删孟”所暴露的,正是一个因背靠国家机器、手握生杀大权而膨胀者的狂妄,他极欲按照他个人对君王与臣民关系的理解,建立一种“新道统”。这种“新道统”的要害唯在于,哪怕恶法,也是法,即使暴君,也是君,“法”和“君”的绝对权威不容丝毫置疑,更不允许反抗。不仅不准反抗,连消极躲避做一个隐士的自由也是没有的,孔子认为读书人在天下无道时可以做隐士,而朱元璋则执行“不合作则死”,连这种消极自由也蛮横取消了。
从此,朱元璋不再满足于做一个世俗政权里的国王,而且还要做“教主”。他对臣民思想的钳制是无孔不入的,他的发号施令不仅局限于政治、经济、军事领域,连臣民的生活方式,包括服饰、器皿、居处、往来称谓、婚丧嫁娶的礼俗等,都要过问和监管。比如他特制一种束头发的网巾,取“万发皆齐”“万法皆齐”相谐,正与其专制心理相合,遂颁行天下,全国百姓都要服用;又如他因为对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不满,便下令学校里不得诵读《战国策》……和儒者争夺道统的话语权,朱元璋们肯定是会成功的,不是别的而是因为他们握有权力。到了清朝的康熙,就更牛了,他径直宣告:“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从此只有皇帝才是最大的理论家、思想家,只有圣旨才是判断一切是非曲直的标准,传统儒家在君权之上的道统被彻底颠覆。“国王即教主”、“权力即真理”的格局正式形成了。
原载《湘声报》2008年10月10日
鲁迅愿当“国学大师”吗
宋志坚
网络时代的花样很多,“新鲜出炉”的令人目不暇接。一会儿是富豪的排行榜,一会儿是最喜爱的华语作家的公选,一会儿又有“十大国学大师”的网评。据说鲁迅的入选引起了各界强烈争议,“‘鲁迅算不算国学大师’,成了这场争议热点中的焦点”,这便多少使我感到有些“新鲜”。
参加网评的是网友,卷入争议的已是学者。读了反对鲁迅入选的和赞成鲁迅入选的理由,却觉得争议的双方都有失水准,甚至还显得有些滑稽。反对鲁迅入选者认为,国学大师对国学的研究一定要深要透,要成为专家,“鲁迅不但没有做到这点,还推行白话文毁灭文言,怎么能算是国学大师呢?”鲁迅确实是力主现代人用白话文的,如果认为文言就是国学,能使文言大行其道的就是国学大师,那么,“怎么能算是国学大师”的恐怕也不仅是鲁迅了。且不说胡适反对用文言写作的力度与鲁迅相当,你去排一排,在评出的这十位之中,有几位生前还用文言写作?
这些年来“国学”被喊得震天价响,“国学大师”的头衔也日趋时髦。令人遗憾的是往往没有弄清什么是“国学”,就在那边起哄。章太炎是人们公认的国学大师。据说他提出的国学的主体部分就是“义理、考据和辞章”;据说他与梁启超等人提出的“国学”的主要内容是包括训诂、文字、音韵在内的“小学”以及“经史子集”。据此而论,恐怕就不能轻言鲁迅“没有做到”对国学之研究“要深要透”。蔡元培评说鲁迅“著述最谨严徒非中国小说史”:《中国小说史略》既在“经史子集”的范围之中,自当毫不客气地在国学之中占有一席之地。他的《汉文学史纲要》对经、书、诗的研究之“深”之“透”恐怕也很少有人可以企及,况且他“本受清代学者的濡染,所以他杂集会稽郡故书,校嵇康集,辑谢承后汉书,编汉碑帖,六朝墓志目录,六朝造像目录等,完全用清儒家法”(蔡元培语)。在这方面的成就还与他的创作翻译被人并称“三绝”。直接受业于章太炎的鲁迅,其小学、经学以及文言根基都相当深厚。仅就国学水准以及对国学研究方面的成就而论,将他与其他几位并称为“国学大师”,不相称的还不知该是什么人呢。
支持者则指出,鲁迅不但有巨大的文学成就,还有深邃的鲁迅思想,传统文化方面底蕴也很深厚,所以当选“国学大师”当之无愧。其实,文学成就巨大,可以称之为文学家;思想深邃,可以称之思想家;传统文化方面的底蕴之深厚,或许也正是他之成为文学家和思想家的一个重要因素。诸如此类,都不是鲁迅可以称为“国学大师”的依据。说得靠谱一些是清华大学的一位刘姓教授,他列出的“评选鲁迅为‘国学大师’的四点理由”虽如蜻蜓点水,却都还沾得上边。然而,我之认为赞成鲁迅入选为“国学大师”的一方也同样“有失水准,甚至还显得有些滑稽”,主要的还不在于其理由是否充足,倒是在于有没有必要为鲁迅去争这个头衔。问题并不只在于鲁迅算不算“国学大师”,还得看看鲁迅当不当“国学大师”。
有反对者认为鲁迅“曾努力贬低传统,对国学也没有推崇。这好像不是国学大师应有的态度”,说这话的好像是人大国学院的院长助理,对鲁迅的偏见是显而易见,但这话也有可取之处。鲁迅确实反对过所谓的“保存国粹”,他不希望将中国文化当做专供洋人鉴赏的古董;鲁迅也不赞成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引导年轻人都“踱进研究室”去“整理国故”,就是国学之研究也与众不同。蔡元培在说他“完全用清儒家法”之时,便指出“惟彼又深研科学,酷爱美术,故不为清儒所囿”。鲁迅对待传统,也是采取“拿来主义”的,当然不会盲目地推崇。如果说,这“不是国学大师应有的态度”,那么,这样的“国学大师”,他确实是不屑为之的。章太炎先生晚年“身衣学术之华衮,猝然成为儒宗”,鲁迅就很为他惋惜和不取。
鲁迅活着的时候,不屑于当这样的“国学大师”,在他去世七十年之后,却有堂堂专家学者汗流浃背地在那边争论他算不算“国学大师”,如此这般,岂不滑稽可笑?!
原载《南方周末》2008年2月7日
清朝文字狱阴影下的《红楼梦》
吴营洲
朋友写了篇文章,题目是《清朝文字狱阴影下的名著》,开头一段是这样写的:
每次把清王朝酷烈的文字狱和那些光芒万丈的小说联系在一起时,我就常常涌起一点困惑。直白而言,我不知道如何把文字狱的惨烈和无孔不入与辉煌的创作成就和谐地统一起来。按理说,在文字狱遍地的年代,人们应该噤若寒蝉,同时斯文扫地,研究枯败,创作凋零才对,怎么会有《儒林外史》、《红楼梦》、《镜花缘》这样的佳作出现?
我对《儒林外史》、《镜花缘》的写作情形,不大了解,无法置喙,而对《红楼梦》的成书过程,倒是略知一二。
诚如朋友所言,“清朝文字狱规模之大堪称中国古代文字狱之最”,“在清朝立国的268年里,发生了160余起文字狱,平均一年半一次”。清王朝“平均一年半一次”文字狱这话,自然没错,但值得注意的是,自乾隆元年至乾隆十六年,一起文字狱都没有(所谓的两起则是雍正朝遗留下来的)。而《红楼梦》这部书,恰恰是在乾隆七年至乾隆十七年这段时间写成的。因此我常常想,如果没有乾隆朝初期这十六年宽松的政治氛围,《红楼梦》很可能就胎死腹中了。
乾隆十六年夏天,发生了“假托孙嘉淦奏稿案”,乾隆才一改他的宽容政策,采取了比雍正更为严酷的手段,大兴文字之狱。此后32年间,文字狱多达l30起。
其时,《红楼梦》业已基本完成。鉴于骤起的压城黑云,为了避祸,《红楼梦》的批评者脂砚斋不得不在书的前面,加上了一大段“凡例”:
书中凡写长安,在文人笔墨之间则从古之称,凡愚夫妇儿女子家常口角则曰“中京”,是不欲着迹于方向也。盖天子之邦,亦当以中为尊,特避其“东南西北”四字样也。
此书只是着意于闺中,故叙闺中之事切,略涉于外事者则简,不得谓其不均也。
此书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笔带出,盖实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也。又不得谓其不备。
……开卷即云“风尘怀闺秀”,则知作者本意原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并非怨世骂时之书矣。虽一时有涉于世态,然亦不得不叙者,但非其本旨耳,阅者切记之。
这样的说辞,当属实情。《红楼梦》的确不是“怨世骂时”之书。曹雪芹的思想境界远远高出了“怨世骂时”。但是这样的说辞,若在“文字狱”前,肯定是苍白无力的。雍正八年,翰林院庶吉士徐骏(康熙朝刑部尚书徐乾学之子、顾炎武的甥孙)在奏章里,错把“陛下”写成了“狴下”,雍正一见,立马就革了徐骏的职。随后,又在徐骏的诗集里,翻出了“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等语,雍正认为是存心诽谤,照“大不敬律”,遂对徐骏“斩立决”。和“清风不识字”相较,《红楼梦》里的“碍语”,恐怕要“反动”得多。“成则王侯败则贼”,“脏唐臭汉”(连汉唐都是脏臭的,其他朝自不待言),“那见不得人的去处”,“拼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任何一条都能令曹雪芹死无葬身之地。庆幸的是,乾隆并没有问罪《红楼梦》。不然的话,晚年的曹雪芹恐怕连喝粥的份儿都没了。
自乾隆大兴文字之狱起,32年间,他制造的冤狱占了整个清王朝此类冤狱的百分之八十。由此便可感知到当时的恐怖。朝野人人自危,士子噤若寒蝉。这在曹雪芹心理上造成的阴影,恐怕也不难想象。
那天又与朋友通电话,我说:你的文章写得极好。你结尾处写的“文字狱下的名著不仅仅是名著,而且是含着血和泪的名著”尤为精辟。可是,清朝文字狱对《红楼梦》最大的戕害,是破坏了这部书的完整,使我们无法看到八十回之后的文字。曹雪芹是写完了或基本写完了《红楼梦》的,就因为八十回之后的文字,涉及到贾府败落、被抄等大的关节,恐为朝廷不容,曹雪芹才生生地给砍掉了。所谓的“借阅迷失”,不过是掩人耳目而已。当然,这只是我的看法。
原载《湘声报》2008年2月22日
杀人与吃人
徐怀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