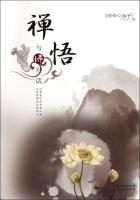但对孟子来说,二分法却应当这样设定:一方是致力于利益,另一方是致力于将“仁与义”确定为行动的动机(这里所说的动机,关注是“应当做什么”,而不论何人或何物会成为行动的对象)。有一种观念认为,在把道德建立在对于利益的追求之上时,会引导人们支持“普遍的”利益,而不是特殊的利益,不过这是一种梦想。墨子本人也感到有必要引入兼爱这一中介原则,以便引导人们为了公共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利益;罗尔斯也指出过,即使是西方的功利主义者,也会感到有必要引入无法解释的“同情与仁慈”(sympathyandbenevolence)原则。毫无疑问,惠王简单地假设他应该能够依靠他的大臣和士兵的忠诚,即便他们本人不能从战争中获得任何利益。但是,为什么他们就不应当关心自己的利益呢?因而,墨子坚持认为,家庭本身就代表着一种特殊的自我利益,对于墨子固执己见的见解,孟子认为,从理想上讲,正是在家庭的怀抱之中,人们才学会了将德性自身作为目的的动机而行动的习惯,而不是将德性自身看作不可告人之目的的手段的动机而行动。由于人类具有这种根据“正确原则”(whatisright)行动而不计其后果的能力,才使得美好社会的梦想成为可能。作为儒家,孟子当然没有抛弃人类普遍福利的目标。他的论辩大体说来是这样的:只有在预设了将“仁义”作为目的本身,并依照仁义而行动的反映人类本质的能力之后,才能取得优良的社会后果。只有完全为正确的东西所激励的人,才能在长远的意义上造就出一个优良的社会,哪怕偶尔也会出现管仲那样的着名人物,他们能够取得某些符合仁德的成果,而不论其动机和手段。看来他们似乎能够“借用”仁的成果。然而,此类不具备仁道动机的仁道成果有可能像浮尘一样,转瞬即逝。
孟子的中心任务是要证明:在面对充满疑惑的世界时,优良社会的实现完全取决于好人(goodman)的内在道德意向。然而,在孟子的时代,这一任务的完成不能简单重复孔子的训示。尽管那些置身于儒家传统之内的人可以接受这一命题,仍有两个问题变成激烈争论的焦点:人们——尤其是那些必须成为社会伦理先锋队的人——怎样才能成为好人,他们应该怎样依靠其伦理品质去改变社会。在墨子着作中所描述的那些近似于子夏观点的儒者们至死都坚持认为,礼乐的实践是使仁德内在化的惟一途径,尽管孔子认为,不具有任何内在灵魂气质的礼乐是毫无意义的形式主义。他们对于内在的灵魂气质是否能影响他们时代的世界这件事似乎不抱什么信心。当然,墨家完全不愿意“向内”进行省察,他们事实上还预设了一种“自然状态”,在其中,个人有机体最初是完全按照自私的样式而被造出来的。因此,根本不存在任何道德的“内在”根源,人们必须接受这样的教育:从功利主义的立场看,兼爱是必须的。由于“性”这个词告诉人们,只要找到道德行为的根源,它的提出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尽管儒家可以泛泛地接受一种公共的道德指令——它是和君子的本性内容相关的公共概念,然而,人们再也不能回避道德的本体论来源的问题。
很显然,到了孟子的时代,儒家圈子里就人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辩。
告子相信,人性既不善也不恶。其他人则相信,有些人生来就是善的,而另一些人生来就是恶的。还有一些人相信,随着“文王和武王的兴起,人们就被赋予善的本性;而随着幽王和厉王的兴起,人们就被赋予残忍的本性。……其他人相信,有些人的天性本善,还有些人的天性本恶。”(《孟子·告子上》:“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这里有种类齐全而各不相同的观点,有的认为道德范畴甚至不适用于个体的有机体,它们完全是“社会”创造的观念,还有的简单地把道德禀性(propensities)看做是不同遗传天赋的结果。顺便说一句,后一个观点,即使它可以同儒家关于道德实体的传统概念相吻合,也似乎能有效地否定人们试图使整个社会“儒家化”的信念。
尽管整个争论似乎围绕着本性的“善与恶”展开,但“性”却只是一个范畴,这一范畴最终要演变成为围绕着人类现实(既包括社会方面也包括个人的方面)的本性而展开的涉及到多种范畴的极其复杂的争论。
孟子的哲学人类学很显然,孟子坚信,只有当人类认识到此类行为的根源和能力就潜藏于他们自身之中,即潜藏于与生俱来的“自然”取向或人类有机体的“本性”之中,人们才能依据纯粹道德动机发出的指示行事。这一论点明显地展现于他与告子的着名争论之中。
尽管人们试图将告子与《墨子》中的同名人物联系在一起,但告子的事迹仍是模糊的,我们对他几乎一无所知。在新儒学(Neo-Confucianism,译者按,指宋明理学)的文献中,由于下面谈到的原因,他常常被认定为道家。
然而,一旦我们将注意力集中于辩论的内容本身,就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他所持有的“客观主义的”价值体系所反映的内容不是儒家的。关于什么是恰当行为的问题,就其争辩中所讨论的具体语境而论,孟子和他似乎根本就没有分歧。真正重要的分歧完全集中于道德根源的方面。
尽管刘殿爵和其他学者已经做了很多疏通性的工作,要对这场争论进行解释仍是困难的。这一段相当精彩,它代表着把当时逻辑辩论法讨论中的流行观念应用到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中的努力,在此方面它堪称典范。下面我试图提出对这场辩论的理解。
告子坚持认为,人性是那种“生而有之的东西[以及对所有的生命都是共同的东西]”(生之)。他随之又作了专门说明:所有生命所共有的、“生而有之”的惟一禀性是食欲和性欲。大致说来,所有其他东西都是由环境造成的,只有这些所有生命都共有的性质才是人类生下来就已“内化了的”东西。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就是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由“外在的”[外]文化内化而成的。然而,他继续说,尽管“仁是内在的,义(righteousness)却是外在的”(《孟子·告子上》:“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这里所说的“仁”,如果赋予它《论语》中那种极其崇高的意义,反而有点令人困惑。在上下文中,它所指的似乎不过就是自然情感(naturalaffections),不但可以和性的吸引力紧密关联,而且还可以引申为适用于族类纽带的内容——我们在其他动物身上终究也能发现自然感情。“义”指的是文明人在任何复杂的生活环境中正确行动的能力,不可能导源于任何内在的本能或者先天的、直觉性的能力。它完全建立于个体把“来自于外面的东西”
(fromoutside)加以内在化、依靠学习而获得的行为规则之上。因而,尽管我们可以拥有对亲族里的老年人表示敬意的“自然感情”,因为他们是我们的亲戚,但我们并没有与生俱来地尊敬作为抽象人类的老年人的天生禀性(propensity),即使儒家道德中有这类尊敬老人的律令也是如此。“有一个老年人,我把他当做老年人[加以尊敬]。这并非是因为我在我自身中先有了把他当做老年人加以尊敬的倾向,这与我对如下事实的认识是一样的——我认识到他的皮肤是白的,是由于我有能力感受到他身上潜存的白性(whiteness)。正因为白性[就像把老年人当做老年人加以对待的规矩一样]来自于外面,我才把它作为白加以认识。”(《孟子·告子上》:“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
“尊敬老年人”的规矩并不来自于任何内在的冲动,只有从外面才能获得(尚不清楚究竟是来自强迫还是来自教育)。尽管告子并不否认道德规定,但是,我承认,他还是提出了某种非常类似于格尔兹所断言的观点。“文化模式……是信息的外在[重点号是我所加]根源。关于外在这个词,我的意思仅仅是——例如它不同于基因——在所有人类个体生来就居于其中的、共同理解的、互为主体性的世界中,它们位于人类个体有机体本身的边界之外。”“文化”是一种把生来仅仅是人(man)的尚未定型的个体有机体转化为人类的一员(ahumanbeing)的独立而自主的领域。如果我们认为他有可能相信儒家传统道德律令的普遍有效性,那么应该不会赞同格尔兹的文化相对论。他会用普遍性的术语来讨论文化中的规矩。
作为儒家的一员,孟子也相信礼的“客观”规定性,甚至还相信人们必须学习礼。然而,他同时还有一个强烈的信念,即:我们所学习到的东西原本就是属于自己的,因为“礼”最终不过是一种就像整个身体有机组织一样内在于人类有机体之中的“仁义”能力的外在表述而已。他也明显相信,只有当人们懂得,正确的东西就内在于他们的“本性”之中,才会履行其作为道德行动者的责任。因而,他必须用一切可能的武器来反驳告子。他问告子:他的所有与生俱来的“本性”概念——所有生命所分享的共同财产——是否与所有白的东西皆是白的这一断言相同?在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他又问:是否说所有东西皆是白的,就等同于说因为人们也享有动物的某些性质,所以人们就“只是”动物?当告子作了肯定的回答之后,他又逼问:“一件白的东西的白性,是否与白雪的白性,以及白玉的白性起的作用相同?”(《孟子·告子上》:“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在他看来,答案显然如此。这里发现了共同的性质,它们是众多物体所共享的性质,但我们全都同意,这些物体之间的差距之大超出了人们的一般想像。它们所共享的只是一个谓词(predicate)而已。孟子接着问:“那么狗的本性与牛的本性是相同的吗?牛的本性与人的本性是相同的吗?”他的论点是清楚的。某些共同的性质可以属于所有动物的种类,但足以使它们区分开来的性质可能才是关键性的特征。
在此我反对葛瑞汉的一个分析,它原本是完全可以根据某种很类似于我们的类的逻辑概念加以讨论的。某几个物类共享了某种共同的性质,这一事实就构成对类加以定义的理由的基础充分吗?当然,告子可以坚持认为,性欲和食欲是人与生俱来的基本特性,因为它们是人类共享的。但是,为什么人们必须假定只有共同享有的特性才是与生俱来的呢?为什么那些将人们区分开来的特征就不可以是与生俱来的呢?那种使我们把它们划归不同物类的巨大差别(牛与狗之间的差别)正是区分性的特性。在此所说与生俱来的差别(异)就不如与生俱来的相同(同)重要吗?既然在对动物的“本性”进行界定时差别是重要的,既然我们认识到这些差别是与生俱来的,那么,有什么理由断言那些使得人类和其他动物(特别是在给定了这些差别的特殊本性的情况下)区分开来的东西就不是与生俱来的呢?说实在的,有什么理由认为人和动物所共享的特性就比那些使得动物区分开来的特性更为重要和基本呢?
整个讨论使人们回想起墨家逻辑学中处理马和牛的物种分类的那些段落,惠施也提到过“巨大的差别”(大异)和“很小的差别”(小异)、极端的相同和很少的相同问题,公孙龙还关注过“白马非马”的问题。人们会突然产生一种感觉,即现在的这些命题和“格言”仅仅是些残篇,如果能够获得全部文献,我们就能发现它们与那个时代的现实问题之间的实际关联。
然而,告子及其弟子继续向如下的观点提出挑战:人们有可能在任何天赋的道德禀性中找到关于正当行为之规定的根源。告子的一位门徒问道:
“假如村中的一个人比你哥哥大一岁,你尊重谁?”孟子的门徒回答说:“我的哥哥。”“[村里的仪式中],在向杯子里倒酒的时候,你先给谁倒?”“先给村里人倒。”“但是,你真正尊重的却是前者——你仅仅把后者作为年长者加以对待而已。这表明,它[正确的行为]是外在的而不是内在的。”(《孟子·告子上》:“乡人长于伯兄一岁,则谁敬?”曰:“敬兄。”“酌则谁先?”曰:
“先酌乡人。”所敬在此,所长在彼,果在外,非由内也。)人们可以说,对某人哥哥的尊敬,是自然的家族性情感的延伸,因而它是“内在的”。在村里办事的场合中,年龄的确要比家族血缘纽带更为重要,但其中蕴藏的规矩所依据的不是任何内在的道德冲动,它只是服从于“习得的”外在规矩。
孟子的回答,本质上乃是尊敬的情感不仅指向具有固定的角色和地位的个人。存在着严肃的场合和特定的环境,人们的尊敬感是从场合自身的本质特性中引发出来的。在村里的仪式中,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年长者这一群体,在这一场合下,人们的尊敬感集中于年龄。孟子所说的道德可以说是非常重视“情境导向的”,事实上,他非常强调“义”,而不是机械地执着于固定不变的“礼”的具体规矩。在任何道德行为中,人们都不只是学习既定的“游戏规则”。这种游戏规则产生于人类根源深厚的天赋禀性,不仅包括对人的感情,还包括对特殊情境的意义的感觉。所有的规矩都可以在某种自然的禀性中找到其终极根源。
然而,与告子的争论并没有穷竭孟子的“哲学人类学”的多方面内容。
它所做的仅仅是为他的如下信念建立了“逻辑的”基础:他相信个体人类肌体组织之中潜存着天赋的向善趋势。
为了描述这一天赋之善,还必须查看其他段落。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很快发现,人心/心灵(心)的范畴肯定和“性”的范畴同样重要。最终说来,“性”只是孟子为了建立人类的复杂形象时所需要的词汇表上的一个术语。
事实上,“心”是使得人类和其他动物区分开来的那部分本性的终极“处所”(locus)。如果正确地加以理解,“性”只是人心(heart)朝向充分实现其道德能力的天赋趋向。的确,孟子在处理人的问题时,其问题意识(problematique)的中心实际上并不是本性(性)而是人心/心灵(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