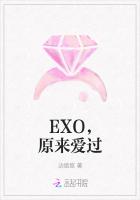旁观王一生进行“车轮大战”的“我”心里涌起的是一种很古的东西:“平时十分佩服的项羽、刘邦都目瞪口呆,倒是尸横遍野的那些黑脸士兵,从地下爬起来,哑了喉咙,慢慢移动。一个樵夫,提了斧在野唱。”阿城写王一生下棋,肖疙瘩护树,王福抄字典,是要写出一种老老实实的人生,诚诚恳恳的态度,发掘出一种贯注于中国文化和历史中的“气”。王福写作文,自言自己发愤读书是因为父亲是一个不能讲话的人,“所以我要好好学文化,替他说话”。某种程度上,阿城创作的《棋王》《树王》《孩子王》等小说,写知青是其次,替“哑了喉咙”的普通百姓和中国文化说话才是真义。张承志的创作,本质上始终有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但他在《金牧场》里,仍借叙述人之口写下了这样的话:“我只是记得在那两年里我劳动过。我只是牢牢地记得:活在底层的人是多么艰难。”知青运动的最大功绩,也许就在于让一代人真正同社会的底层有了接触,认识到真正的人生和中国文化是什么样子。陈村说自己“是从农村开始认识人生的”,张抗抗也曾谈到自己在北大荒的两个发现,并说“正是那两个幼稚而真诚的发现,开拓了荒野上曲曲弯弯的小路;开拓了我的一生,开拓了一个属于我们的时代”。韩少功在《远方的树》中借田家驹的视角写道:“每个土房黑洞洞的门里,都有陌生的男女老少,都有忧和乐,有历史和现实,有艺术的种子和生活的谜。”王安忆在《69届初中生》中借雯雯上调县城的机会写道:“最主要的是,雯雯从此吃上商品粮了,每月有定量,三十一斤半粮,半斤油。有了这份商品粮,今后一辈子的生活似乎都有了基本保证。雯雯从小吃着它长大毫不觉得什么,而当它失去之后再重新获得的时候,便深深体会到了它的可贵。”韩少功后来从事“寻根”文学的提倡与创作,王安忆后来在《喜宴》《开会》《青年突击队》
等作品中以一颗平常心去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应该说与他们的知青经历都有紧密的联系。在谈到史铁生小说创作中的宿命母题和玄思特色时,人们通常溯源到他的身体残疾,但从《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插队的故事》等作品来看,底层百姓那种强烈的生存意志同样是形成其作品中与命运抗争母题的一个重要精神资源。
“寻根”文学的提倡与创作是知青作家最后一次以群体形象集体亮相。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后,随着中国文学创作由一元化文学向多元化文学发展,作为一个创作群体的知青作家的影响力开始减退,但其中的一些佼佼者如王安忆、韩少功、张承志、史铁生等,其个人的影响力开始逐渐增加。当然也有一些曾为人们看好的知青作家,由于创作乏力而淡出文坛。文学创作就是这样,作为一项艰苦而又寂寞的事业,不进则退,这是谁也无法反抗的规律。
三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在经历了伤痕、反思、改革文学创作潮流之后,中国作家开始面临两种不同的道路选择:一是继续沿着早几年有关现代派文学讨论中徐迟等作家的思路,走一条文学的现代化即等于文学的现代派化的路;一是像韩少功等作家那样,转而寻找东方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势,走一条文学的现代化即等于文学的民族化的路。尽管从具体的理论表述和创作实践来看,当时作家们的选择并不像这里所概括的一样泾渭分明(他们在立论时都以文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为前提,只是在如何走向现代化和世界化的具体途径上出现了分野),但作家们的不同创作取向确实也引出了文学创作潮流的不同流向。如果说,寻根文学潮流表现出了对中华民族文化精神自我的寻求,以刘索拉、徐星、残雪、余华、马原、莫言、苏童、格非、孙甘露、北村、吕新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则广泛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表现手法,或描绘现代人的孤独感与荒诞感,或揭示人的非理性的生存本质与生存之烦,或演绎个人的、家族的传奇故事,或挖掘人的原始的生命强力,并对文学的文体形式与表现方式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实验,从而酿成了声势浩大、令人瞩目的先锋文学潮流。
先锋作家大部分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们虽然也经历过“文革”,但他们不是“文革”的真正的参与者和受害者,“文革”灾难只给他们留下些模模糊糊的记忆。他们真正的成长时期已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所接受的文化教育和思想资源同“归来”一代作家和知青一代作家相比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最明显的是,俄苏文学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对这一代作家的影响渐减,欧美文学特别是欧美现代派文学、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对这一代作家的影响渐增。在王蒙、张贤亮、蒋子龙、刘心武等作家那里,苏联文学和世界无产阶级文学曾是他们重要的文化资源,《青年近卫军》《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等作品曾被他们反复提起,干预现实的热情和影响人灵魂的创作冲动在“归来”一代作家身上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引领文学风潮的那段日子里,这些作家虽然从自身的经历和过去的历史中得到教训,十分反感政治对文学的干预,呼唤文学的多元发展,但在创作中却表现出极大的政治热情,希冀以自己的创作推动政治的拨乱反正和历史的正本清源,虽然他们有时也表现出对文学审美特性的短暂眷恋,但干预现实人生和政治的巨大热情常常使他们热衷于载道文学、问题文学的创作。对他们来说,个人是不重要的,也是渺小的;文学只有在同党派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结合在一起时,才能体现出其价值;让文学回到文学本身既是他们难以理解的,也是他们力所不及的。这一代作家后来虽然也参与了中国文学人道主义话语的建构,甚至尝试过带有现代派色彩的创作,但比起更年轻的作家来,这样的创作活动始终停留于带着脚镣的跳舞,自己感觉到总有些放不开手脚,读者看上去也总觉得有些局促。
知青一代作家在所接受的文化资源上虽然同“归来”一代作家有所不同,但这种不同远远小于先锋作家与“归来”一代作家的差异。
张承志、张炜等作者,虽然更多地将眼光投注到了托尔斯泰、罗曼·罗兰等作家身上,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等创作仍给他们以重要的影响,对理想、信仰、崇高的追求仍是他们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只不过他们不像“归来”一代作家那样,将对理想、信仰、崇高的追求落实为对一具体的党派和国家的忠诚之上,知青一代作家的追求有一个更纯粹、更高远的目标,并且倾向将对大众利益的追求与个人的自我实现结合在一起。同“归来”一代作家和知青一代作家相比,先锋作家的创作明显呈现出了边缘化和个人化的倾向,“归来”一代作家所熟悉的所谓重大题材是与他们无关的,他们的写作多游移于生活的边缘地带,笔触大多在现实和历史的缝隙里游移徘徊,生活的主体部分被他们忽略了,然而,人们也注意到,先锋作家所忽略的不过是生活的表面真实,他们更热衷于生活和历史的深层真实的发掘,对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世界的挖掘拓宽了文学世界的深度和广度,对普遍人性的关注和形而上主题的表现,使他们获得了比“归来”一代作家和知青一代作家更广阔的文学空间。先锋作家均是以十分个人化的方式进入创作的,他们的创作走向极端时,甚至带有情绪独白和语言游戏的倾向,既不写个人感觉和记忆以外的事,也不为文学以外的目的而创作。他们的晚出使他们先天地获得了前代作家通过艰苦挣扎和奋斗得来的成果与自由,他们不必再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一类恼人的、无趣的问题去喋喋不休地争辩和忐忑不安地担忧,他们可以明目张胆地主张文学的自足独立而不需承担以往作家必须承担的政治风险。时代既给纯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外部生存环境,他们中的大多数也主动选择了纯文学的创作立场。
先锋作家的创作离不开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在他们的创作中明显存在着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借鉴和模仿,其创作也堪称“文革”后中国文学不断向西方开放而获得的成果。在王蒙创作所谓“东方意识流”小说的时期,作家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借鉴是谨小慎微的,中国式的主题加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技巧,是王蒙《春之声》、茹志鹃《被剪辑错了的故事》、宗璞《我是谁》等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春之声》运用意识流手法,写工程物理学家岳之峰坐“闷罐子车”回乡途中的见闻和联想,作品虽然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让岳之峰视通万里,思接千载,用意识流连接起了过去和现在、外国和中国、城市和乡村,但这种意识流动与吴尔芙、乔伊斯、普鲁斯特的意识流创作有本质的不同。这是一种经过理性过滤和驯化的意识流描写,所有的意识流动都指向最终的极端理性化的中国式主题:“如今每个角落的生活都在出现转机,都是有趣的,有希望的和永远不应该忘怀的”。《我是谁》从表面看与卡夫卡的《变形记》和西方那些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创作有相同之处,但它的创作灵感显然来自“文革”时期人妖颠倒、人沦落为牛鬼蛇神的现实,其主题表达也是纯粹中国式的:“只有‘人’回到了自己的土地,才会有真正的春天。”在关于意识流的通信中,王蒙曾一方面将意识流手法中的联想法同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兴”等同起来,一方面还不忘强调说:“我们的‘意识流’不是一种叫人们逃避现实走向内心的意识流,而是一种叫人们既面向客观世界也面向主观世界,既爱生活也爱人的心灵的健康而又充实的自我感觉。”作家们在这时的处境是颇为尴尬和局促的。他们在表达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认识时,一方面迫不得已地认同于当时的主流解释,表明其精神是腐朽的、堕落的,因而要忙于划清界限;同时又要强调其手法是新颖的,有用的,或与中国文学传统手法有暗通、神似之处,因而不能全盘排斥。在一些倡导现代派文学创作的理论文章中,这种一分为二的尴尬表述尤为明显。徐迟策略性地在经济的现代化与文学的现代派化之间建立简单的同步关系,预言“不久将来我国必然要出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最终仍将给我们带来建立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两结合基础上的现代派文艺”。冯骥才一方面热情洋溢地主张“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同时又强调这个现代派是广义的,“即具有革新精神的中国现代文学”。徐迟的“拉郎配”式的论述方式和冯骥才的将“现代派”文艺泛化的倾向,与其说是源于对现代派文艺的不理解,不如说是出于在一个仍对西方文化保持着高度警惕和排斥态度的时期所采取的论述策略。而当马原、余华、苏童、格非等作家登上文坛、从事具有现代派色彩的文学创作时,世风已经大变,“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不仅在理论上受到了怀疑,而且从读者审美接受的角度说也多少显得有点不合时宜。
在年青作家和批评家那里,言必称现代派文艺已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时髦。从“文革”后中国作家借鉴现代派文艺的渐进过程来看,黄子平的一种理论概括是有道理的。他说:“在仍处于开放过程的社会,‘异质’的文学思潮的传入可能经历这样一些反应阶段:
1.被视为完全的异端遭到绝对拒斥;2.部分‘非实质性’的因素(如技巧、手法等)被容纳;3.经由与本土文学传统的相互调整产生了‘化’的契合点;4.成为本土文学传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果说,“文革”后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派文艺的吸收和借鉴最初还有些谨小慎微、畏首畏尾,稍后的学习和模仿还有些生吞活剥、粗糙生涩,那么,到了1985年以后,当大批先锋作家登上文坛以后,现代派文艺应当说已成为中国本土文学传统的一个有机部分了。
同前代作家主要从空间维度考虑西方现代派文艺与中国文学之关系不同,先锋作家主要是从时间维度来考虑西方现代派文艺与个人创作间的关系。西方现代派文艺被视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产,也成为先锋作家必须加以超越的文化大山。在卡夫卡、福克纳、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作家面前,先锋作家普遍有一种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巨大的求新的冲动支配了他们的创作,探索实验的热情使得他们无暇去关注文学的外在使命。甚至后来理论界关于“伪现代派”的讨论和指斥也没有对这批作家的探索热情形成大的影响。而这种探索热情本质上是一种文学的求新冲动,先锋作家并不需要像理论批评家们那样树立一个什么“真”的现代派目标、然后再向那一目标勇猛冲刺,他们只是想写得与前代作家和同代作家有所不同。有人戏称那段时间的作家被一只创新之狗追得连站下来小便的时间也没有无疑是十分生动形象的。先锋作家确实比以往任何时候的中国作家表现出了更大的艺术上的创新求新冲动。在《虚伪的作品》中,余华甚至不单纯将小说的传统局限在狄德罗、巴尔扎克、狄更斯,而扩大到了20世纪的卡夫卡、乔伊斯、罗布格里耶、福克纳、川端康成,其中蕴藏的创作野心无疑是不言而喻的。“归来”一代作家那种对现实人生的关注热情,知青作家那种对理想的高度礼赞和苦苦追寻,在先锋作家那里衍化成了自我实现和自我迷恋的巨大欢欣。正像人们已经注意到的,在“归来”一代作家那里,“我们”这个关键词通常是指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党;在知青作家那里,通常指我们这一代人;而到先锋作家一代,“我们”这个关键词则被“我”所取代。先锋作家更热衷于个人化的文学世界和文学话语的建构。当然,这并不是说,先锋作家已完全脱离了同社会政治、民族国家、文化传统间的联系。在残雪的《苍老的浮云》《黄泥街》《突围表演》,余华的《一九八六》《历史与刑罚》,格非的《追忆乌攸先生》,苏童的《独立纵队》
等创作中,我们均可以看到刚刚过去的民族灾难在作品中的折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