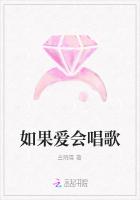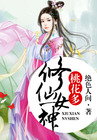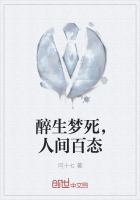将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运用于现代文学评论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刘西渭。
刘西渭(李健吾,1906—1982)在1936年和1942年先后出版现代文学评论集《咀华集》和《咀华二集》(上海文化出版社),集子里的不少文章经常将所评论的中国现代作家作品与西方近现代作家作品进行比较。例如在评论沈从文的《边城》时,刘西渭说:巴尔扎克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但不是一个艺术家,福楼拜却是一个艺术家的小说家,而“沈从文是一个渐渐走向自觉的艺术的小说家”。他又将乔治桑与沈从文对比,认为“乔治桑是一个热情的人,然而博爱为怀,而且说教。沈从文是热情的,然而不说教,是抒情的,更是诗的,《边城》是一首诗,是二佬唱给翠翠的情歌”。
在评论巴金的《爱情三部曲》时,刘西渭认为:“巴金缺乏左拉客观的方法,但是比左拉还要热情,在这一点上,他又近似乔治桑”;“乔治桑仿佛一个富翁,把他的幸福施舍他的同类,巴金先生仿佛是一个穷人,要为同类争来等量的幸福”。在评论曹禺的名剧《雷雨》时,刘西渭指出:曹禺隐隐地受到两出戏的暗示:一是希腊尤瑞彼得司Eurpides的Hippolytus,一是法国辣辛Racine的Phadre。都出于同一故事:后母爱上前妻的儿子。前后两个故事中后母遭到前妻儿子的拒绝,《雷雨》中,后母遭前妻儿子的捐弃。这三个故事的“同一气息是作者同样注重妇女的心理分析,而且全要报复”。刘西渭又认为,曹禺把周冲这个人物写失败了,比不上法国戏剧家博马舍的《费嘉洛的婚姻》中的谢瑞班。在讨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时,刘西渭提出,这是前苏联法捷耶夫的《毁灭》给了他一个榜样,并具体分析了萧军和法捷耶夫在风景描写、情节安排、艺术效果上的不同。此外,刘西渭还将夏衍的《上海屋檐下》与果戈理的《两个伊凡的吵架》、日本作家滕森成吉的《光明与黑暗》作了比较品评。刘西渭以一个西方文学翻译家的慧眼多识,以一个作家的敏锐感受,将比较文学的方法和理念贯穿于当时正活跃着的中国作家的批评中,为比较文学与文学评论的结合做出了成功的尝试。
(第四节)跨学科研究的尝试
研究外来的宗教、哲学等非文学的因素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属于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的、“超文学”研究,或称“跨学科研究”。1920—1940年代,一般的“跨学科研究”已有所起步,如朱谦之在《中国音乐文学史》中对音乐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宗白华在一系列文章对书画之关系的研究等。其中,朱谦之的研究局限在中国文化内部,没有跨文化;宗白华的研究虽然常有跨文化的中西比较,但基本属于艺术学、美学的研究而不是文学研究。从比较文学学科的角度看,此时期朱维之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之关系的研究,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的“跨学科”同时又“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
关于宗教与文学之关系的研究,此外有关学者在中印文学关系研究中对佛教与中国文学之关系,已多有涉及。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之关系,周作人在《圣书与中国文学》(《小说月报》12卷1期,1921)将基督教“圣书”(即《圣经》)与中国的经书作了对比,并指出了《圣经》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是探讨这个问题的较早的一篇文章。而朱维之(1905—)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学关系的文章,并出版了题为《基督教与文学》(上海青协书局1941)的专门著作,后又推出了题为《文艺宗教论集》(上海青协书局1951)的专题论文集。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做了深入探讨,成为此时期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特别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中的最有代表性的成果。
关于《基督教与文学》一书的价值,刘廷芳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
基督教在文学史上的成绩巨大,而且重要,这是尽人皆知的。然而论者只能举其大概,至有系统的论述,在基督教先进国中,也不多见。朱君此编,在我国实为空前的第一部著作。
这里点出了《基督教与文学》一书在我国学术研究上的开创性,是中肯的。实际上,在所谓“基督教先进国”的欧美国家,关于基督教及其与文学之关系的研究,早有大量著作,但一般都是以教徒的身份姿态,站在基督教立场上所作的研究,而那时的朱维之似乎也是一位“基督徒”,但他的研究却是纯学术的,这就显示出他的特异性来。他研究宗教与文学之关系,首先就是基于对文学与宗教渊源关系的深刻认识,他在该书“导言”中开门见山地说:“从原始时代以来,艺术和宗教一向是不可分离的。
我们现在若要研究古代文学艺术,便不能不涉及古代宗教,研究古代宗教也必须从古代文学艺术里去探求。”又说:“宗教本身便是艺术,因为宗教本身重在感情和想象,一如艺术,宗教的热情等于艺术的灵感;宗教的表现也就是艺术的表现。我国歌舞戏曲始于巫风,希腊悲剧始于葡萄神祭礼,中世纪基督教礼仪发达为宗教剧,作为近代剧的张本,明证宗教仪式也是综合艺术的鼻祖。”基于这样的认识,朱维之在《基督教与文学》一书中,始终以文学的眼光看基督教,又以基督教的眼光看文学。以文学的眼光看基督教,他得出了“基督教是最美、最艺术的宗教”,以基督教的眼光看文学,他认为“伟大的文艺作品是基督教所结的果子”。可贵的是,他对基督教的文学价值的高度估价,不只是处于对基督教本身的认同感,而是有着更深刻的文学与文化的动机。他认为:
中国固然已有悠久的文化历史,有特殊的、丰富的文学遗产,但那只是旧时代的贡献,祖宗的努力。现在我们成了新世界的一环时,亟需新的精神,新的品格,新的作风,来做新的文学贡献。新文学中单有异教的现实面是不够的,我们更需要基督教的精神元素。现在基督教对我国文学青年作精神上的挑战,对我们民族品格挑战,要在我们的文学里注入新的血液。
可见,朱维之的根本用意,就是通过基督教与文学之关系的研究,在中国文学中“注入新的血液”。20世纪初、特别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不少中国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自觉或不自觉的“注入”了基督教的“血液”,丰富了中国新文学的风格与意蕴,现在朱维之通过学术研究的方式,明确提出“输血”,是与中国新文学的基本精神一脉相承的,也体现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宗旨。
《基督教与文学》全书约十八万字,分七章,前五章从不同角度论述基督教《圣经》的文学价值,例如在第二章《圣经与文学》中,他论述了《圣经》对后世西方文学的影响,指出:希伯来人的《圣经》与希腊史诗悲剧,“同为欧美文学源泉,好像《国风》和《离骚》为中国文学的渊源一样。后代文学都汲取于它而得滋生化养”。同时,他也指出了《圣经》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介绍了《圣经》汉译的大体情况。他认为,在中国最成功的《圣经》译本“当然要算是官话和合本的新旧约全书。这译本恰好在我国新文学运动前夕完成,成为新文学运动的先锋”。
这一看法与此前周作人在《圣书与中国文学》一文中的看法是一致的。在第三章《圣歌与文学》中,朱维之不仅论述了基督教的圣歌(又称赞美诗)在西方文学的地位与影响,同时还论述了圣歌的翻译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对使用圣歌的体式“创作圣歌的新诗人”,如刘廷芳、赵紫宸、谢扶雅、顾子仁、杨荫浏、杨镜秋、许地山等人的创作做了评论,并指出了“圣歌”对中国新诗的“合乐”性和格律化的借鉴作用,这大概是第一次对中国的“圣歌”创作所做的评论,直到今天都不失其新鲜感。在第六章《诗歌散文与基督教》和第七章《小说戏剧与基督教》中,朱维之对基督教对西方诗歌散文和小说戏剧创作的影响做了大体的描述,也指出了中国新文学家,如周作人、谢冰心、许地山、苏雪林、张若谷等诗歌散文创作所受基督教的影响,对苏雪林的《棘心》和老舍的《老张的哲学》与基督教的关系作了分析。尽管朱维之对这些问题的论述还是初步的,但他毕竟较早地、系统地指出了基督教与中国新文学之间的关系,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具有开拓性。1980—90年代,有五六部公开出版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关系的博士论文,这些论文的学术渊源无疑都可以追溯到朱维之的《基督教与文学》。
在《基督教与文学》一书出版后,朱维之继续关注宗教与文学问题的研究,在1940年代的十年间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到1951年,作者将这些论文结为《文艺与宗教论集》正式出版。
《文艺与宗教论集》共收二十二篇文章,其中有研究宗教与文学艺术之关系的论文,也有研究外国作家及其与宗教关联的论文,还有关于景教的几篇考据性文章。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较有价值的是《高尔基论宗教》、《艺术的真实——马克思论文艺与宗教》、《中国基督教黑暗面的几个镜头——读肖乾的〈栗子〉》、《中国文学的宗教背景》、《雅歌与九歌》等,从上举前两篇文章看,朱维之研究宗教(包括基督教)的立场发生了一些悄悄的变化,在《基督教与文学》中,他对基督教的亲近和弘扬态度是没有掩饰的,但《文艺与宗教论集》中的有关文章,表明他已经一定程度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对宗教的看法,这使他的研究更带有科学与客观的色彩。《中国文学的宗教背景——一个鸟瞰》一文,对中国古代文学与原始宗教、儒教、道教、佛教、基督教的关系做了粗略的钩勒,似乎是一本专著的写作提纲。最值得注意的《雅歌与九歌——宗教文艺中的性爱错综》一文,作者对《圣经》中的《雅歌》和中国屈原的《九歌》做了比较分析,认为两者都是宗教文艺作品,都有性爱的内容,在体裁上也很接近。这样的类同研究尽管还显得有些简陋,但作为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的平行研究,朱维之的这篇文章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第五节)翻译文学的理论探索
自从1898年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的命题之后,我国翻译界对翻译的原则标准、翻译的功用、翻译方法等,开始了探讨。这种探讨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全面展开,由此前的一般的翻译论而集中于文学翻译论,文学翻译成为翻译理论问题的中心。所探讨的问题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对翻译文学之作用的认识
此时期中国文坛所发生的显著变化之一,表现为不但在实践上更重视翻译文学,而且在观念上也确认了翻译文学的价值,对翻译与创作的关系的看法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那时,作家与翻译家兼于一身的情形已十分普遍,作家翻译家们在翻译与创作的双重实践中意识到,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必须借助外国文学的翻译;要创作出不同于以往的“新文学”,必须向外国文学学习;翻译与作家自身的创作相辅相成,是与创作同等重要的文学实践活动。
主张翻译文学为文学革命、为新文学的建设服务,以翻译文学来颠覆原来的文学系统,以建立新的文学系统。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之一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一文中,第一个正式发出大力翻译外国文学名著的号召,并且将这作为“创造新文学”的唯一的“预备”和“模范”。他说:“创造新文学的第一步是工具,第二步是方法。方法的大致,我刚才说了。如今且问,怎样预备方才可得着一些高明的文学方法?我仔细想来,只有一条法子:就是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鲁迅在《关于翻译》(1933年)一文中认为:“我们的文化落后,无可讳言,创作力当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比较的薄弱,是势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时时取法于外国。所以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决不可压抑了一面……”
不过,那时人们对文学翻译的认识也只停留在它对中国文学起到“模范”的作用,对中国作家的创作起到推动的作用。而“文学翻译”本身有没有“文学”的独立的艺术价值?换言之,“文学翻译”是不是“翻译文学”?人们的认识并没有到位。所以,一味从文学翻译的这种外在作用看待文学翻译,势必会导致只把文学翻译视为手段,视为媒介和工具。关于这一点,郭沫若(1892—1978)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在《论诗三札》(1921)中,对当时国内问题翻译与创作的不平衡状况发泄了“一些久未宣泄的话”。他写道:
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凡是外来的文艺,无论译得好坏,总要冠居上游:而创作的诗文,仅仅以之填补纸角……翻译事业于我国青黄不接的现代颇有急切的必要,虽身居海外,亦略能审识。
不过只能作为一种所属的事业,总不宜使其凌越创造、研究之上,而狂振其暴威。翻译价值,便专就文艺方面而言,只不过报告读者说:“世界花园中已经有了这朵花,或又开了一朵花了,受用吧!”他方面诱导读者说:“世界花园中的花便是这么样,我们也开朵出来看看吧!”所以翻译事业只在能满足人占有冲动,或诱发人创造冲动,其自身别无若何积极的价值。而我国国内对于翻译事业未免太看重了,因之诱起青年许多投机心理,不想借以出名,便想借以牟利,连翻译自身消极的价值,也好像不遑顾及了。这么翻译出来的东西,能使读者信任吗?能得出什么好结果吗?除了翻书之外,不提倡自由创造,实际研究,只不过多造些鹦鹉名士出来罢了!
在这里,郭沫若将“创造”与“翻译”对立起来了,把翻译看成是“附属的事业”,认为只有“消极的价值”。说到底,也是把文学翻译看成是“创造”和“研究”的参照和手段,即不认可翻译文学的独立价值。在这一点上,他和上述林纾、鲁迅等人的看法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但将翻译比作“媒婆”,创作比作“处子”,对翻译的贬低溢于言表,因而在当时和此后都引起了争议。
郑振铎在当年6月发表了一篇题为《处女与媒婆》的文章,对郭沫若的上述言论提出了批评。郑振铎指出:“处女的应该尊重,是毫无疑义的。不过视翻译的东西为媒婆,却未免把翻译看得太轻了。”他认为郭沫若说的当时翻译已凌驾于创作之上,“狂振其暴威”,是一种“观察错误”,言过其实。次年2月,郑振铎在《介绍与创作》(《文学旬刊》1922年第29期)一文中再次提到了“媒婆”论,他指出:“翻译的功用,也不仅仅是为媒婆而止。就是为媒婆,多介绍也是极有益处的。因为当文学改革的时候,外国的文学作品对于我们是极有影响的。这是稍微看过一二种文学史的人都知道的。无论什么人,总难懂得世界上一切的语言文字,因此翻译事业实为必要了。”郑振铎不仅不满意把文学翻译比喻成“处女”和“媒婆”;而且还进一步把文学翻译看作是新文学的“奶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