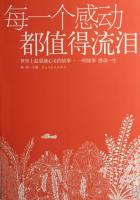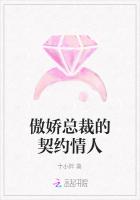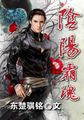他认为,最近为止,英国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始终集中在前现代的材料上,如果说现在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现代文学作品做了他们学汉语的教材,“因此英国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尚处于‘婴儿期’。”在第九章中,作者对中国文学在英国的传播情况做了总结和展望。他指出,“总的印象是,中国文学在英国的传播并不理想。这不需要也并非同我们自己悬想的标准相对照;相反,只要和美、法等国做一点平行的比较,就能觉察出来。文学传播的基础在于汉学的发达。没有哪个汉学不够发达的国家,在译介中国文学方面会做出显著成绩来。”作者接着指出,好在英国的汉学家们对此已有清醒的认识,1989年出版的《独一无二的疲弱——英国汉学史》一书,就引发了人们对英国汉学的反省与思考。我们可以期望,今后中国文学在英国的传播会出现新的局面。
张弘在《中国文学在英国》一书中,体现了自觉的明确的方法论意识。在该书的《余论:影响研究的形态学方法》中,他提出了“形态学的方法”,即注意文学在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发出的种种形态上的变异,即“文本形态”、“诠释形态”和“想像形态”这三个层次的形态的变异现象。在《中国文学在英国》一书,作者特别注意了中国文学的原本的“文本形态”与经过英国人的独特的理解与译介之后形成的“诠释形态”,乃至英国人超越文本自身,从自己的文化视域出发的所做出的“想当然”的结论,即“想像形态”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其衍化的过程、原因。这种方法看来是科学的、切实可行的,也是颇为成功的。
但另一方面,作者又拘泥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现有的概念,认为自己的《中国文学在英国》这样的研究属于“影响研究”。实际上,该书属于中国文学在英国的“传播研究”,而极少涉及中国文学对英国文学的“影响研究”。“传播研究”关注的是传播过程中的“形态”的变异,而“影响研究”关注的是作家创作中外来影响与独创的关系的研究分析,亦即作家作品的审美分析。张弘的《中国文学在英国》对中国文学在英国的传播,做了系统详实的评述,尽管有些问题由于资料的限制,论述得还不充分,如英国文学中涉及中国题材的作品,现有的论述还是粗陈大概,但作为比较文学在英国的“传播研究”的成果,该书在选题上和研究中所体现出的首创性,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结实的存在。
二、英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的研究
中英文学关系研究的另一方面,是英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的研究。80—90年代,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百多篇论文,选题集中在莎士比亚、王尔德、萧伯纳、劳伦斯等作家在中国的传播及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其中,关于莎士比亚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成果最多。20年来,有关文章已有五六十篇。在这些文章中,有莎士比亚与中国作家的平行研究,如莎士比亚与汤显祖、关汉卿、李渔、纪君祥、曹雪芹及其相关作品的比较研究,也有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传播问题的研究。平行研究的文章中有代表性的是方平的几篇论文,如《王熙凤与福斯塔夫》(《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曹雪芹与莎士比亚》(《文艺理论研究》1981年第3期)等,这些文章后来都收进了作者的论文集《三个从家庭出走的妇女——比较文学论文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中,由于方平本人是莎士比亚的翻译家,对莎士比亚的作品相当熟悉,故文章中常有独到的感悟和见解。
但一般来说,由于平行研究在可比性问题上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莎士比亚与中国作家的平行比较就很难超越同异比附的僵硬模式,学术价值也难以确认。关于莎士比亚对中国文学、中国作家影响问题的文章,也出现了若干篇。如曹树钧的《田汉与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理论与创作》1995年第3期)、《莎士比亚与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郭沫若学刊》1993年第1期)等,认为莎士比亚的戏剧对田汉、郭沫若的戏剧创作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但在论述的过程中难以列出充分的事实依据,而更多地依赖于对作品形式与手法的相似性的对比分析。在这种情况下,也有学者的论文提出不同的看法,如李万钧在《比较文学视点下的莎士比亚与中国戏剧》(《文学评论》1998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莎士比亚对中国戏剧家诸如曹禺、田汉、夏衍、老舍等的影响甚为微弱,无法与易卜生、契诃夫、托尔斯泰、高尔基、古希腊悲剧、奥尼尔乃至王尔德相比”,“究其原因,用一句话说,就是莎士比亚离我们太远,易卜生等和我们相近”。
李万钧所说的莎士比亚对中国戏剧家的创作影响不大,是一个可靠的结论。但他所分析的原因则不尽然。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现代戏剧所关注的是社会问题、时代问题,而不是莎士比亚所关心的那种超越时代与社会的人性问题。这恐怕是莎士比亚与中国现代戏剧家之间最大的隔膜。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及戏剧文化史上,才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接受现象:一方面对莎士比亚非常赞赏,大量译介,大量上演,在艺术上莎剧也被糅入中国的传统戏曲中;一方面在创作上,尤其是在创作的内容上,却很少接受他的实在的影响。这样,在莎士比亚与中国的比较研究中,关于影响的研究就很少,而更多地集中在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传播的研究方面。
这方面的研究在我国最早开始于50年代以后。8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文章逐渐增多。较有价值的文章大都是从翻译文学及翻译文学史的角度,对莎士比亚的各种中文译本进行比较分析;或者研究朱生豪、梁实秋等在莎士比亚作品翻译上的贡献,如吴洁敏的《朱生豪与莎士比亚》(《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2—3期)、朱生豪夫人宋清如的《朱生豪与莎士比亚戏剧》(《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期)、许祖华的《梁实秋对莎士比亚的翻译与研究》(《外国文学研究》1995年第2期)等。
鉴于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的演出、翻译、评论形成了较长的历史传统,积累了丰富的遗产,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学术史,学术界称为“莎学”。对中国的莎学进行总结性的研究,就成为莎士比亚与中国关系研究中的十分重要的课题。80—90年代,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可贵的成果。先是出现了有关的资料集乃至学术专著,如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编辑的《莎士比亚在中国》1987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收集了有关导演和专家学者黄佐临、陆谷孙、马焯荣、曹树钧和孙福良、汪义群、胡伟民、熊国栋等人的12篇文章,是一部集中探讨莎士比亚戏剧在我国舞台上的演出与中国观众的审美需求之关系的文集。
1989年,哈尔滨出版社出版了曹树钧、孙福良合著的《莎士比亚在中国舞台上》,该书是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演出历史的专著。从1902年莎剧第一次在我国上演算起,莎剧在中国舞台上的历史已有一百年,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莎剧在中国的演出规模越来越大,1986年京沪两地还举行了盛大的“莎士比亚戏剧节”。在这种情况下,从戏剧艺术和戏剧文学的角度,系统地清理莎士比亚在中国舞台演出的历史,对于总结我国翻译、改编和上演外国戏剧的历史经验,对于丰富中外戏剧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莎士比亚在中国舞台上》一书,以大量丰富的史料,优美流畅的文字,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国戏剧舞台上的莎士比亚戏剧演出史、接受史、与中国固有的戏剧文化的融合史。
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莎士比亚与中国的戏剧创作》,从戏剧文学的角度探讨了莎士比亚对中国现代话剧创作的影响。第二章和第三章《莎士比亚在中国舞台上》(上、下),把中国的莎士比亚戏剧演出史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早期话剧(文明戏)时期(1907—1918年),二、现代话剧诞生和初步发展时期(1918—1949年),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影响下的莎剧演出时期(1949—1965年),四、冲破禁忌、精彩纷呈的时期(1978年后)。在第四章中,作者以《空前的盛会——首届莎士比亚戏剧节》为题,记述了1986年中国举行的震动中外文化界的首届“莎士比亚戏剧节”的盛况。第五章《莎士比亚戏剧与中国的话剧教育》,专门探讨了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的话剧教育中的地位、作用与价值。第六章《戏曲改编莎士比亚剧作的初步经验》,介绍了以戏曲改编莎士比亚戏剧的各种形式和方法,探讨了“戏剧味”和“莎味”的结合问题,认为以昆曲、越剧等形式改编和移植莎士比亚戏剧是成功的,是繁荣中国戏剧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书后还附有《莎士比亚在中国舞台上演出纪事》等四种资料性附录。《莎士比亚在中国舞台上》一书向读者表明,从20世纪初莎剧被改编成“文明戏”开始,到30年代以后正规化的、高水平的演出,再到80年代后莎士比亚戏剧成为在中国上演最多、改编最多的外国戏剧,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中外戏剧文化交流的深化和中国戏剧文化的繁荣。贺祥麟先生在《评〈莎士比亚在中国舞台上〉》(《外国文学研究》1991年第3期)中认为:“《莎士比亚在中国舞台上》是一本有关莎剧在中国演出和莎学在中国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小小‘百科全书’。这样的书,不但应在我国出版,还应该译为外文,向国外介绍。”同时也遗憾地指出了本书编校粗糙,错字过多的问题。
1994年,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孟宪强的《中国莎学简史》。这是中国“莎学”的总结性著作,对中国莎学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做了系统全面的总结与评述。此前,孟宪强编辑出版过《中国莎士比亚评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选收了1917—1989年的70年间我国学者撰写的莎士比亚的评论文章30多篇,可以看成是《中国莎学简史》的前期成果。《中国莎学简史》分为“综述”、“分述”、“附录”三个部分。在“综述”部分中,作者从纵向的角度,描述了中国莎学的历史进程。
他把中国莎学分为六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发轫期”(1856—1920年),第二个时期为“探索期”(1921—1936年),第三个时期是“苦斗期”(1936—1948年),第四个时期是“繁荣期”(1949—1965年),第五个时期是“崛起期”(1978—1988年),第六个时期是“过渡期”(1989—)。以上六个时期的划分和梳理是清楚得当的。尽管有些阶段的划分略嫌琐碎。如20世纪80—90年代,作为一个时期来看,也许更恰当;对某一时期特点的概括用语也有进一步斟酌的余地,如“崛起期”似乎不如称作“复兴期”,“过渡期”也不如称作“总结期”或“深化期”。但总的看来,他的划分是能够正确反映中国莎学发展演进轨迹的。
《中国莎学简史》的“分述”部分,从横向的角度,就某一方面的问题加以专题评述,其中包括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舞台演出、评论、教学与研究、学术团体的建立及其活动、首届莎士比亚戏剧节的情况等。并在相关专题之后附有“莎士比亚作品中文译本”的目录,“中国上演的莎剧剧目”一览,“中国莎士比亚研究著作、文集、辞典、译著”目录,“中国莎学机构与团体”等重要的文献资料。这一“分述”部分将“综述”部分的问题做了进一步展开,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与“综述”部分在资料上过多重复使用、重复论述的问题,影响了学术著作应有的洗练。该书的第三部分,即“附录”部分有《中国莎学人物小传》、《1917—1993年中国莎评四百篇选编》、《中国莎学年表》等三种资料。总体来说,《中国莎学简史》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莎学的“小百科”,是20世纪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的一个详细的总结,也是近二十年来我国中英文学关系研究及中英文学比较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一项成果。
除莎士比亚外,中英文学比较研究中被重视的课题还有拜伦、王尔德、萧伯纳、狄更斯、乔伊斯等英国作家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的研究。所涉及的接受这些英国作家影响的中国作家有苏曼殊、鲁迅、郭沫若、田汉、郁达夫、老舍、巴金、梁遇春等人。
重要的文章有邵迎武的《苏曼殊与拜伦》(《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汪文顶的《英国散文随笔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影响》(《文学评论》1987年第4期)、张祖武的《英国的Essay与中国的小品文》(《外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2期)、张振远的《“中国的爱利亚”——梁遇春》(《中国比较文学》1995年第1期)、袁荻涌的《郭沫若与英国文学》(《郭沫若学刊》1991年第1期)、辜也平的《巴金与英国文学》(《巴金研究》1996年第2期)、夏骏的《论王尔德对中国话剧的影响》(《戏剧艺术》1988年第1期)、沈绍镛的《郁达夫与王尔德》(《文艺理论与批评》1996年第4期)、耿宁的《郁达夫·王尔德·唯美主义》(《外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1期)、李冰霜的《笑的艺术——谈老舍的幽默艺术与狄更斯的创作》(《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1期)、王友贵的《乔伊斯在中国:1922—1999》(《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2期)等数篇。由于中英作家之间事实联系的材料很有限,许多文章不得不将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结合起来,有的则完全是平行研究,如赵砾坚的《哈代与沈从文的逃避主义》、周国珍的《罗伯特·彭斯及其中国读者》(均刊《中国比较文学》1991年第2期)等。
由于缺乏实证或无法进行实证研究,有些文章不免流于空泛。但其中也有佳作,如《论王尔德对中国话剧的影响》就是一篇长达三万余字的有分量的、高质量的论文。该文论述了五四时期中国文坛对王尔德及其戏剧作品介绍、翻译、评论、研究及对中国话剧所产生的影响。文章认为,在中国新文学的发轫时期,王尔德是作为世界重要作家之一最先被介绍到中国来的。那时中国文学界对于唯美主义文学的理解主要是依据对王尔德的艺术主张及其作品的译介。在王尔德的全部作品中,最被中国现代作家所注意的是他的戏剧和童话,而剧本《莎乐美》更是得到了广泛的评论和借鉴,对五四时期的中国话剧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其中,向培良的剧作《暗嫩》所受《莎乐美》的影响最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