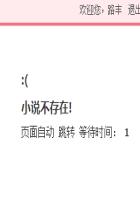纽约华尔街股市的交易大楼内人们有点近乎疯狂地在大厅内噪闹着。华莱士带着盈利的喜悦踮起脚望着电子显示板,他情不自禁地用手拍打着手中的公文包。
又是一个星期五的交易日,连续的牛市使所有的交易者都满怀欣喜。可以看出纽约的这个圣诞节将是一个繁荣的节日,人们的消费热情也空前高涨。华莱士从交易大厅出来已经有一个多小时,但还没有从赚钱的喜悦中跳出来。他排在食品店购买火鸡的队伍中居然格格地笑起来,惹得许多人观望。当他无意识地向窗外扫视了一眼,却真切地发现一驾马车定格在玻璃的窗格子内,这个景象好像只属于他,其他人依然做着自己的事。当他定睛看时,发现那架马车向他的这个方向在移动。在他关注窗外的片刻,周围的男女被他的这个状态吸引住了,没过多长时间,所有的人都将目光投向马车出现的那扇玻璃。其实,这家食品商店正对着大街,像一幅透视图那样两边的建筑由大及小地立列两边,映衬着马车在这里的显赫地位。被这种突然而至的事件夺去片刻的宁静后,人们才开始依据自己的判断去选择接下来的行动,但更多的人跑到街上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华莱士也跑到街上并且挤在最前面,他从衣兜里掏出手机向妻子汇报街上发生的事情:“喂,丹尼。我在街上看到了一架上个世纪的马车,不,19世纪,不,18世纪的马车,不对,这绝对真实,原来我们只是在教科书上才能看到的马车。现在它已经过来了……我也不知怎么回事,路上所有的车辆都靠边行驶,不是幻觉,车厢里还坐着两位漂亮的女人,她们好像非常恐慌……”
华莱士环顾左右,发现人们的脸上充满了好奇。
马车上的女人相当的焦虑,她们在半路上丢掉了她们信赖的向导胡福,现在,马车又将她们带到了她们从未认可的世界,至少,她们认识的故乡不是这个样子。就在没有来到纽约华尔街之前胡福使者就渐渐地淡化了,她们一直盯着的绿色屏障也渐渐随着胡福的消失而没有了影子。
两位旅伴在相互询问对方:“失去胡福后我们该做怎样的选择?”
“你说胡福还会回来吗?”唐娴问。
厄休拉默不做声地看着眼前,眼泪静静地从脸颊上滑落下来,小声地表示:“我们永远也找不到家了。”
“胡福还会出现吗?”唐娴又问了一遍。
唐娴的问话还是没有得到回答。她能够解答的比自己强不了多少,这是她知道的,可是最先占领问话权的似乎能够从危机中找到安全港,这对厄休拉来说多少有些不公平。一路上不都是受胡福调遣吗?什么时候她能够决定自己的行程?现在,胡福消失了,故乡的影子也消失了,对于这样的变故,使她们同时都掉进了无底深渊,失落的痛又加上唐娴投过来的依赖使她无法忍受。她们默不做声地机械地跟着老马继续向前,等厄休拉委屈平复之后才甩给唐娴一句话:“你说胡福还会回来吗?”
“我在问你。胡福没了,又一次没了。命运会把我们抛到哪里?”唐娴也觉得受到了进攻。
“你认为我和胡福私通吗?要是我也这样认为会怎样。”厄休拉埋怨道。
唐娴才知道胡福的消失使她们这对漂泊的人产生了隔膜,她赶紧回避这样的疑问:“我没这个意思,胡福一直被我认为是一个命运的依赖,比起来,你比我更坚强些,由于我更脆弱才问你胡福的下落。厄休拉,请原谅我。”
“娴,或许我们很快就会到了故乡。”厄休拉顷刻就从埋怨中和解了。她给唐娴带去宽慰:“现在我们只能跟着老马向前。好在老马还不停地走着。不要太多地往坏处想。”
旅伴的和解并不意味着各自真的减轻了心理负担,胡福使者的消失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让她们困惑。如果说已经接近到了故乡,胡福的消失一定令她们多少年来深信不疑的身份产生了怀疑。这就证明她们的行程最终是被欺骗的,那个胡福就一定是假的。然而,这样的不辞而别留给两个人致死不明的困惑,换个说法,应该说是神背叛了人更适宜,悲惨的是,两个旅伴可不这样认为,她们开始自责,她们长时间地垂着头回顾着自己的过失,看看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使者。她们的确找不出自己有违背胡福的地方。有时候也抬起头透过胡福坐在的位置看看到了哪里。她们的眼神里流露出对于胡福的渴望,希望这种担忧是多余的。
唐娴提醒厄休拉注意:“我们现在根本看不到更多的景象,周围布满灰白色的晨雾,只有眼前那么一点道路还能够被分辨出来。”
“是的,我们究竟到了那里?”厄休拉附和着。她把目光投向老马,久久地看着那匹熟悉的老马出神。自从她登上回家的道路,胡福与老马就一直陪伴着她们,虽然胡福在路途中不断地变换装束,有时候看来有意遮掩自己的形象,可是老马却始终是那个样子,不过能够看得出,它现在的步履有些蹒跚,跋涉起来非常吃力。胡福在时谁也没有对它有什么更多的关照,现在,看着它那样的执着,那种视死如归的精神,她由衷产生了爱怜之心。她拉了一下垂头丧气的唐娴:“你看,那匹老马对我们多么忠诚,有它在就一定能够把你我送到故乡去。”
受到提醒,唐娴才对一直在她们身边的老马重视起来,她充满温情的表示:“以前,它没有在我们的眼里,但它像空气那样围在我们身边,老马,快带我们回到故乡去吧!我累了,你也累了,到了终点让你我快乐地休息……”
厄休拉笑了:“瞧,诗人与我在一起。”
唐娴也笑了。紧张的气氛放松了许多,老马的身影和它不屈的脚步给她们宽慰。虽然经过一路风尘,虽然胡福骤然消失掉了。但车厢里依然还保持着温馨,路程还在行进中。她们只能沿着这种感觉走下去,没有其他选择,那些路途中的遭遇,不管是事实还是梦境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那些都是胡福安排的。
就在她们听天由命地继续她们的行程时,忽然几片白色的纸钱自马车的正前方飘落下来,打在了窗玻璃上,惊得两个人顿时睁大了眼睛。许久,她们没有对话,但她们知道这是从哪里飘来的纸钱。虽然胡福消失了,但纸钱却代表使者的信息。
“故乡离我们已经很近了!”唐娴居然这样地大声宣布。
厄休拉不解地用眼神询问来由。唐娴进一步解释道:“看到那些纸钱,好像看到了许许多多熟悉的面孔。这些景象已经是久违了,我小时候胡福撒下的纸钱。”
厄休拉这才安静地表示:“到家了。”
当迷雾渐渐散去,她们始感到她们的马车行进在由灰色的高厦相拥起来的路上,唐娴揉了揉眼睛,期待着眼前的景象清晰起来,然而,能够被分辨出来的除了像一道高高的绝壁那样的灰色的影子矗立在眼前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影在下面晃动。不时的出现幻影,被幻影吸附到其中的景象已经是在她们的旅途中司空见惯的事,这一次在她们看来也没有什么意外,只不过胡福已经离开她们有很长的时间,她们没有办法向他求证是否这又是旅途中的一次幻觉。她们只能耐心地贴着窗子仔细辨别她们究竟到了哪里。
时间久了,两个女人好像也看出来大道旁闪烁着一些朦胧的五彩缤纷的亮光。一阵风袭来,她们的马车发抖似地颤动着,当然,那些白色的纸钱还依然有规律地从马车前的空中降落下来。
“厄休拉,我感到心里发慌。”唐娴紧紧地裹着衣襟。
“我也是这样,现在什么都不要怕了。让那个老朋友决定吧。”厄休拉指了指依然迈着沉重脚步的老马。
现在她们没有什么事可做,两个人隐约地预感到最后的审判来临。除了害怕,还夹杂着仅有的一点期待,那就是经过这样提心吊胆与无奈的长时间的旅程,她们有幸见到还没有从心中彻底泯灭的故乡。
在没有回答的等待中,寒风开始试图扯烂她们的依靠——这个一直让她们安心的车厢。她们眼看着周围的缝隙在风的嘶号中变大,惊惧与寒冷使两个本来年轻漂亮的女人变得面如灰土。
有时候失望的情绪会随环境的变化而起伏,车厢被寒风撕扯得随时都有破碎的危险,希望也一下子凋落,在她们失神的眼睛里老马左右摇晃的屁股可能还预示着一丝寄托。
本来厄休拉已经没有热情,但最后她还是惊喜地大叫:“罔高!罔高!”
她挥动着手臂,伸向旁边的窗子,原来是投机商华莱士的脸随着马车的运动贴在窗玻璃上。厄休拉由于过于激动脸上抽搐一下就僵持下来,唐娴拉一拉她的衣服,她没有任何反应。
“你到家了。”唐娴没有任何动情的能力了。她也感到了精疲力竭,任由命运摆布。
最后,马车还是被风尘剥削得七零八落,顶盖没了,四周窗子要么也没了,要么只连着一点随风摇曳。只有纸钱还不时地从空中落下。
唐娴的脸上还残存着生命的印记,然而,在她能够看到那个繁华的都市时却已没有精力再鉴赏一下路途的虚实。在华尔街的街心,排列于两侧的人群中骤然间老朽不堪、形晦枯槁。
欣赏完那架特殊的马车,华莱士重新回到交易大厅,惊讶地发现电子显示牌上所有的数字都是零,自己皮包里的文件都变成了中国人祭奠死者时使用的瞑钱,他惊呼着:“诸位看看显示屏和自己的文件是怎么回事,那架马车把我们的财富席卷而空。”
整个交易大厅都乱了,有的人盯着画满零数目的屏幕发呆,还有的人将手机与手提电脑气急败坏地抛向空中或摔在地上,也有人泪流满面地叫喊着……
华莱士马上想到验证一下自己的信用卡是不是也没钱了,就挤出噪杂的人群,穿过大厦对应出的一条小巷,急不可待的到那家大型的超级市场的收款柜台前验证自己的信用卡。可是,收费的女管理员告诉他:“你不用那样着急。货架上已经没有物品,那些东西都是蜡制的,如果要是来参观也用不着信用卡。”
华莱士相当失望:“怎么可能呢?”
“不过这里不是有划卡设备吗?你可以试试。”女收款员告诉他。
这样,华莱士就反复地在收款机上划自己的信用卡。还是有显示,红色的数字显示出一串零。
“你们能不能修理一下这台收款机,让它显示出数字来。”华莱士请求道。
“我们不再用这台收款机了。”服务员回答。
“就是说我卡里的上千万美元都不能兑现了吗?”华莱士瞪着眼睛问女服务员。
女服务员摊开手摇摇头:“对不起,你去问那些大人物吧。”
华莱士将信用卡摔在了地上,服务员捡起来告诉他:“这可以留个纪念。”
华莱士看到大街上的人在纷纷争抢报纸,也过去看了一眼,大标题是:“十八世纪马车使股市衰亡”,还有:“东方魔女卷走一切”。
过了几日华尔街的人们才平静下来。
《华尔街日报》的编辑们对于记者采编来的新闻图片与说明争论不休,有人提出这样的标题:“世纪前的马车”,也有人提出“木乃伊走进生活”……
总编辑多尔先生一边听着编辑们的争论,一边看着那几帧放大了的图片,最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首先提醒人们注意:“那驾马车的式样显然是十八世纪贵族的马车,两个女人的衣着那样朴实,看来像是丢失了很久,她们在寻找什么,只有回家才能够解释她们是漂泊的人,她们急于寻找归宿,我看叫‘归途’更适宜。”
当人们手里拿到这则新闻在阅读的时候,那架世纪的马车已经离开了这里。人们在议论:“为什么不拦住它,问一问它究竟从哪儿来?到哪里去?”
也有人反驳道:“怎么问?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纪的人,我们不能理解她们的行为。”
自从这架寻找故乡的马车出现后,世界都为之愕然,在东方的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也知道了这则奇怪的新闻,当被预知在今年的夏季,马车将穿过中国古老的皇宫,那里的人们认为一架拉着木乃伊的马车将要来到这里。于是,考古学家、社会学家,还有协和医院的医生们都做好了准备,甚至吴可医生的实验室也提前腾出了一间大房子,定制了特殊的扫描仪、手术器械。这些天他异常兴奋,动辄就告诉他的学生:“要从基因构造上找出木乃伊的来历,从而推断出它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