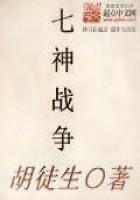“我不是医生。我只是一个魔术师。”沈放对那个右脸上有伤疤的人说。
听沈放这么一说,右脸有伤疤的人立时勃然大怒,把枪口指向了沈放的额头。
“你**的,你是在耍我吗?”
“我怎么会是在耍你呢?”
“魔术师会看病吗?连国际名医李维廉都束手无策的病,你一个魔术师有个毛线用呀?”
沈放清了清嗓子,一本正经、循循善诱地说:
“正因为国际名医都束手无策了,你们才需要魔术师。你想呀,连李维廉这种最出色最有名的医生都检查不出、治疗不好的病,其他医生来了,那也是束手无策。这说明,这个病已经超出了医学的范畴。你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奇迹。谁能制造奇迹,并以此为生呢?”
右脸有伤疤的人想了想,带着些犹豫、带着些不自信地回答:
“耶稣基督?”
沈放差点一个跟头摔到地上。
“我觉得观音菩萨更靠谱一点。你看,观音就住在普陀岛,离这不远……”左脸有伤疤的人严肃认真地插了句话。
这回,沈放真的一个跟头摔到了地上。
毕竟,沈放的腿上是有伤的。
沈放在地上挣扎了两下,想爬起来。
可是,一个腿上有伤、被捆成粽子一样的人,就算再努力挣扎,又怎么爬得起来呢?
“你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去求神拜佛?”
右脸有伤疤那人的声音在沈放的头顶上响起。
他蹲在沈放的头顶旁边,俯视着沈放。他的枪口不经意地擦弄着沈放的脸颊,把沈放的脸弄得痒痒的。
沈放挪动了两下自己的嘴角,缓解了一下脸上痒痒的感觉,然后才说:
“我的意思是,你们应该去找一个会制造奇迹的魔术师。”
“魔术都是骗人的。我们不信那一套。”
听到这话,沈放先是一愣,然后眼珠一转,说:
“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是你们最后的希望。你们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你们那个‘导师’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这世上可没有药店卖治后悔的药。”
听沈放这么一说,那两个脸上有伤疤的人反而不知所措了。
右脸有伤疤的人站起身,把自己的同伴拉到一个角落里,嘀嘀咕咕地不知在商量些什么。
很快,两人似乎达成了某种共识。
他们转回身,把沈放从地上抬了起来。
“我们决定,让你试试。如果救活了导师,我们就放你走。”
“放我们走。”
“对,放你们走。”
“那赶紧把我解开吧。”
右脸有伤疤的人抬手就是一枪。
“砰!”
捆着棉被的绳子应声而断。那个大大的漂漂亮亮的蝴蝶结从正中间分开,犹如蝴蝶脱落下来的两片翅膀一样飘落在地上。
棉被从沈放身上滑落下来。
一股寒风掠过沈放满是汗水的脊背,激得他打了个冷颤。
“好……好枪法。”沈放由衷地称赞。
“小意思。我们搞革命的革命党都是训练有素,对敌人的打击如同外科手术一样精确。不像有些滥竽充数欺世盗名的家伙,想要刺杀贝勒却误杀了个翻译。”右脸有伤疤的人得意洋洋地说。
“是,是,精……精确,训练……训练有素。”沈放结结巴巴地附和。
“说,你要怎么给导师治病?”右脸有伤疤的人随手把枪插回了腰间。
“那个,我们魔术师制造奇迹靠的是魔法。对,魔法!我的魔法是我自己独创的,结合了咱们中国传统的道术,比西洋人的魔法威力大了数倍……数十倍……”
“少啰嗦,快说,你要怎么施展魔法?”右脸有伤疤的人又把手按到了枪柄上。
“我需要一些……很多法器!你们要先帮我把法器准备好了,我才能够施法。”
“说,都需要什么?”右脸有伤疤的人手并没有离开枪柄。
沈放深呼吸一下,努力把目光从那只按着枪的手上搬开,转而投向了昏迷不醒的导师。
良久。
“我需要你们帮我准备一件道袍、一把桃木剑、一盏油灯、一碗清水、四根桃木桩、一条很长很长的麻绳、二十八个黄铜铃铛、黄纸、朱砂,还有一盆黑狗血。”
“……你再说一遍,说慢点,好让我拿笔记下来。”
沈放等着右脸有伤疤的人拿回纸笔,又一样一样地从头说了一遍。
“对了,你还要到城隍庙去,拿一些香灰回来。”沈放最后补充说。
右脸有伤疤的人拿着这份清单出去,留下左脸有伤疤的人看守着沈放和李维廉。
沈放列出来的这些东西,有的固然普通,但像桃木桩、黑狗血这些东西,要是不知道门道,也真十分不好找的。
沈放心里打的小算盘是,把这两个脸上有伤疤的家伙支出去,让他们忙上一阵,自己慢慢想办法脱身。
可沈放没想到,只过了一个多小时,右脸有伤疤的人就回来了。
“怎么这么快?你准备齐全了吗?少准备了一样法器,我都没有办法施法……”沈放诧异地问
“怎么会少呢?你看,道袍、桃木剑……”
右脸有伤疤的人把“法器”一样样排在沈放眼前,果然一件不少。
“怎么样,大魔术师?准备施法吧!”
“呵呵呵……好,好吧。”沈放硬着头皮答应。
那么,问题来了:
沈放会魔法吗?
不会。
他会的是道术。
在沈放很小很小的时候,他的老家来过一个道士。这个道士教给了沈放一些道术。
沈放当时学这些道术的时候,只是觉得好玩。
不管学什么,只要觉得好玩,就会学得特别认真、特别用心、特别快。
当时的沈放就学得特别认真、特别用心、特别快。
沈放的道术学得快、进步得快,却也在沈放的身上留下了后遗症。
一种无法痊愈的后遗症,一种让沈放抱憾终生的后遗症。
所以,沈放后来放弃了学习道术,也一直很后悔学习过道术。
直到今天。
他在那个昏迷着的“导师”身上,看到了一些东西。
一些和他曾经学过的道术有关的东西。
此时沈放的心里是七上八下。
沈放知道,人们学习过的技能分为两种:一旦学会就终身有效的,以及不经常练习就会逐渐退化的。
沈放不知道,道术属于哪一种。
他真的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练习过道术了。
沈放盘膝坐在地上,在脑海中不断回忆着曾经学习过的道术,回忆着每一个细节。
他很清楚,如果自己失败,等待着他的将会是什么。
那两个脸上有伤疤的人站在一旁,一边监视着沈放的一举一动,一边窃窃私语:
“右臂,你觉得这小子靠谱吗?”
“我觉得有戏。你看他,盘腿坐在那,隐隐约约给我那么一种得道高人的感觉。反正,他不是说今晚子时开坛作法吗?他要是真不靠谱,那咱们就……”说着,右脸有伤疤的那人指了指自己腰间的手枪。
“对。等到子时,自有分晓。”
夜半。
将近子时。
之前的十几个小时里,沈放除了吃饭和上厕所,就是在那里盘腿打坐。
他全神贯注地沉浸在自己的回忆里。
在回忆里,时间是停滞的。
在回忆外,时间却是飞逝的。
“大魔术师先生,子时就快到了。”
沈放缓缓睁开眼睛,扫视了一下四周围。
四周围已经按照沈放的吩咐,布置得妥妥当当。
屋子还是白天那间躺着病人的屋子。
这间屋子里是安装有电灯的。但是电灯并没有打开。
用来照明的是屋子四角点燃的数十支蜡烛。
在烛光照射下,屋里的一切虽显得朦胧,却也看得清楚。
屋子里的那些医疗器材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四根桃木桩。
四根桃木桩分别占据着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四个方位。每根桃木桩上都贴着一道符。
一根大麻绳将桃木桩连在一起,圈成了一个正方形的圈。
方圈的每个边上都系着七个黄铜铃铛,一共二十八个。
方圈的中心是一张病床。
病床上躺着那位“导师”。
在他的头顶上摆放着一盏油灯。
室内没有风,灯火却摇摇晃晃。
在他的脚底下摆放着一碗清水。
地面没有震动,水面却不断泛出波纹。
“是时候了。”
说完,沈放就作势要站起,但他马上又坐回到了地上。
腿盘得太久,麻了。
“那个……可以扶我一把吗?”
沈放向右脸有伤疤的人求助着。
“啊?”
那右脸有伤疤的人明显没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就在这时,灯火摇曳得更加剧烈,水面也像沸腾了一样上下翻滚。
“来不及了,快拉我起来!”
沈放的语气仿佛在下命令一般,不容置疑。
右脸有伤疤的人下意识地服从着,一下子把沈放拉了起来。
站起身的沈放连忙披上道袍,右手抓起桃木剑,一瘸一拐地来到方圈旁边。
“铃!”
一个铃铛响了。
那是从西北方桃木桩向西侧数第二个铃铛。
紧接着,西、北两侧的十四个铃铛都“铃铃铃”地响了起来。
“在那吗?”
沈放嘴里嘟囔着,手里抓起一把香灰掷向了西北方向。
只听半空中爆出一阵阵“嘣嘣”声。
一粒粒香灰像一颗颗小型炸弹一样爆炸开。
细小的粉尘炸裂成肉眼难以看见烟幕。
烟幕中,一道红影若隐若现。
在烛光的照映下,沈放看得清清楚楚。
那道红影是一个人的形状。
人的红影。
沈放把手中的桃木剑指向了红影,问道:
“你,究竟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