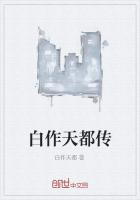§§§第一节电子媒介时代文艺的发展
电子媒介出现以后,图像文化异军突起急剧扩张,使传统的文学阅读和艺术接受遭到了空前的危机,文艺受到了市场和读者的挑战。从创作来看,消费性、娱乐性的类型化写作越来越盛行,各种表演性的、追求媒介效应的行为艺术也大行其道,大众也逐渐接受和认同这种纯消费性的、娱乐性的创作,并热衷于文艺的“媒介事件”。就文艺批评来说,批评家也在追求多元化话语时迷失了基本的道德伦理和价值关怀。于是,关于“图像化扩张”、“文学性的坚守”、“文学的边缘化”、“艺术的终结”和“文艺批评的伦理”等的讨论就成"了近几年文艺理论界的热点话题。我们应该正视电子媒介及其导引的图像文化和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已经对文艺生态形成了客观性的影响,但也应该承认文艺还会向前发展甚至重新迎来繁荣的局面。不过,要发展文艺事业,要使文艺生产为构建精神文明服务,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一、建立和谐的批评生态
和谐的文艺生态是文艺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但和谐的文艺环境的建设,需要作家与批评家对话,作家与作家对话,批评家与批评家对话。同时,年老的艺术家与批评家和年轻的艺术家与批评家之间也要对话。有了对话,就会有相互的理解和包容,同时,有了对话,才能为文艺的发展共同努力。具体来说,建立和谐的文艺生态,需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
1.话语多元与价值一致的问题。30年前,文艺批评曾经出现过“一元话语”和“二元思维”,那是政治意识形态强烈干预文艺创作和批评的结果,属于文艺的非常态。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禁,文化解禁,作家、艺术家的主体创造能力得到了充分的舒展和发挥,文艺创作与批评也越来越自由和多元化。特别是进人新世纪以来,随着电子媒介和数字媒介的兴起,文艺创作与批评有了新的平台和话语空间,文艺批评更加呈现了多元的格局。尤其是随着新闻出版市场放开和中外学术交流的日益增多,西方文艺理论新观点和新著述被大量引进,文艺批评出现了“话语热”,以至于有学者担忧“西方话语”会对中国文学进行殖民而使中国文艺理论失去审美效力。应该说,“话语热”并不是一件坏事,中国文艺理论批评面对新的时代、新的经验,不但需要激发自身的活力,而且也需要在新旧的观念碰撞中得以刷新和更迭自身的理论话语。
但令人担忧的是,文艺批评在强调话语多元时,忽视了价值一致性的思考。在包容多种风格流派和多种审视维度的同时,否定了文艺批评的价值底线和道德关怀。从实际的情况看,许多批评家过于热衷于“话语”的生产,比如贴标签、命名和制造理论批评新术语等,不完全是西方文艺理论的有效借用,所以,与其说是积极地参与文艺建设,还不如说是为了争夺文化权利。因为这些批评家深知,“新的话语”就是一种新的文化符号,而文化场域内部的权利之争就是文化符号权利之争,也就是说,“新的话语”是批评家一种颠覆已有权威的武器,只有“新的话语”能够推翻以往的美学信仰、文化信条和审美尺度,只有“新的话语”能够促使批评家获得文化的支配权。这种对“话语”生产的过分热衷导致的后果,就是一些新的批评面孔进人了文化场域,并获得了一定的文化资本,拥有一定的文化位置,但文艺批评的价值维度就被消解了。可以想象,文艺批评一旦变成了名利场,变成了文化权利角逐的领地,文艺批评家还能坚守艺术的灵魂和操守吗?高小康在一篇文章里,批评过当前文学批评不断创立门派和任意贴标签的现象,他认为“标新立异的分类名称往往因为耸动视听而产生社会影响。这种批评操作对批评家知名度提高的作用自不待说,对作家的作品和出版商显然也有好处。但这些名目越来越多的文学标签对于理解作品却少有帮助,而且常常因为标签含义的模糊或对作家作品风格分类的任意性而遮蔽了具体作品意义的独特性和丰富性,从而误导读者”。
文艺批评的话语需要多元化,而且在正常的自由的文化环境里,文学批评的话语肯定是多元的,但话语多元主要是审视文艺现象的视角不同,透视文艺本质的方法论不同。话语多元并不等于价值多元,并不是评价文艺的尺度和标准的多样化和游移化。如果评价艺术的尺度五花八门和游移不定,就会造成文艺批评失范、失信和失效。所谓失范,就是文艺批评失去基本的艺术尺度和标准,出现人人都有自己的标准,这样一来,文艺的普遍性原则受到质疑,文艺再也不可能形成精神支柱的品格,文坛就会变成一锅乱粥。所谓失信,就是文艺批评一旦失去了标准,就会失去了公正性和可信度,这样的文艺批评不但作家、艺术家不买账,普通的读者也会置若罔闻,甚至不屑一顾。所谓失效,就是文艺批评失去效力,失去对社会文化的建构力和引领力,也会失去对人心世界的熏陶、洗礼与提升。
因此,无论什么样的话语,文艺批评的价值追求应是基本一致的,都是指向文艺精神,指向文艺对社会良知和基本人性的建构。文艺批评再多元化,也不能偏离对创作的审美的引导和社会的批判,也不能偏离对良好文艺生态环境和和谐的社会文化的建设。
2.寻美评论与求疵批判的问题。当前文艺批评之所以为人垢病,作家、艺术家不满意,一般读者也不满意,人们称批评家为“红包批评家”,称文艺批评为“棒喝”,为“赞词”,为“献媚”,为“圈子里的唱和”和“文艺产品推销员”,主要原因是当前文艺批评主要是“寻美”的评论,而忽视了“求疵”的批判。文艺批评失去了其批判精神,批评家的批判道德和批评责任感就会受到怀疑,而且批评家也就放逐了其主体精神,把自己变成了文艺产品和作家、艺术家的附庸。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来审视,这种批评行为也是等于批评家把自己的生命价值和文化位置降低一格,也是有意地把创作与批评置于不平等的地位,这是不符合人性关怀的。
应该说,寻美的批评也是需要的,尤其是对优秀作品进行推广和评介的时候,需要有准确的发现美的目光和缜密的传达美的文字。但求疵的批判更加有用,它是文艺创作的一种“严厉的合作”。正如有人说的:“寻美的批评家是在对读者讲话,是要让他们明白一本古书或新书好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好;他不是在对作者讲话,完全用不着说他们的作品令人称赞。求疵的批评家却是在对作者讲话,他所进行的不是教育公众,而是试图教育作者,他们告诉他们知道,提醒他们,让他们有所防备。他的职能是根据每位作者的气质了解他们应该有的但只要稍加小心就可以避免的缺陷;对于那些不可避免的缺陷,他至少可以掩盖或减轻其严重程度”。可以说,寻美的批评起到的作用主要是引导文学读者进行有效的审美鉴赏,达到指导阅读的目的;而求疵的批判起到的作用主要是对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进行批评和警醒,达到指导创作,引领创作的目的。
当前文艺批评失去批判精神缘于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批评家个人素养不够,本身就缺乏独立的识见,无法洞彻深邃的文学世界和艺术世界,因此无力对文艺现象进行一针见血的批判;此外,一些批评家进入批评的目的并不是建设性,而是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为了满足某种经济利益或其他文化利益。二是文学体制还存在结构性的缺陷。现有的以作家协会和大学中文教育为主体构成的文艺体制应该说在文艺建设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长期以来由于国家把这一体制变成了一个“铁饭碗”,但无法彰显批评家的主体创造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批评家的惰性,削弱了批评家的斗志,因为现有的文学体制、学术体制赋予了某些缺乏创造力和批判精神的“批评家”以无忧无虑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地位。而且现有的文学体制和学术体制也无形中划定了文学的圈子,每一个圈子都是一个利益集团。如以作家协会和创作研究机构为中心结成的批评圈,以大学文学导师为宗主结成的批评圈,以某一个理论批评刊物为阵地结成的批评圈,等等,每一个文艺利益集团的成员之间虽没有明确的行事规则,但面对同一个文艺现象或参与文艺评奖时,彼此都心照不宣,保持态度的一致,有人称之为“潜规则”。肖鹰在审视当前文学批评时,认为当前文学批评呈现出两个矛盾现象:一是批评的缺失,一是批评的过剩。他认为“所谓批评的过剩,则是主流批评群体聚合在媒体周围,以集体的形式向读者发射被选中的作品的‘过剩信息’”。肖鹰所说的“主流批评”其实就是当前文学批评的一个具有话语霸权的圈子,他们聚合在媒体的周围通常以共同的语气来评介符合他们标准或他们乐意纳入他们视野的作家和作品。不难发现,这样的圈子使每一个文艺角色都进人到了基本固定的位置,因此,批评如果不按照基本规则说话,就意味着越位。而越位则意味着招致圈子的进攻或不容,甚至有可能遭遇无形的封杀和抵制。
因此,要恢复文艺的批判精神,一来需要批评家提高个人艺术素养,掌握足够的理论资源,就不会人云亦云;有了充满人文关怀的审美眼光,就不会虚无委蛇,把批评的权利当做廉价的商品出卖。二来需要优化文艺体制,打破现有的学术怪圈和批评小圈子,使批评家从圈子的利益中摆脱出来,解放出来,这样,批评家才能充分地发挥主体创造性,才能发出强有力的批评的声音’而不是发射“过剩的信息”。
3.对话者与审判者的问题。近年来,文艺批评之所以难以得到读者和作家的认同,很大程度上也因为文艺批评没有摆正自己与创作的关系。很多批评家认可了自己法官的角色,以为批评是为创作立法的,而且批评行为就如裁判行为或审判者的言语。这实际是把批评置于创作之上,而变相地把创作视为批评的奴隶。应该说,批评意味着阅读与审视,也需要判断和结论,但这并不意味着批评家就是法官与裁判。批评应该是批评家与作家、艺术家之间平等的对话。茨维坦·托多洛夫曾针对新批评的弊端而倡导过“对话批评”,他说:“批评是对话,是关系平等的作家与批评家两种声音的相汇。”他还批评那些“教条论”批评家根本不让别人说话的霸道:“他是无所不在的,因为他代表着天命或历史规律或另外一个默契的真理。”那些“内在论”批评家“则只是根据一种永远正确的教条阐明:读者是被看成与他观点一致的”。而“结构主义批评又以客观描述作品为金科玉律”。在托多洛夫看来,以内在论为主要特征的新批评和以教条主义为标准的旧批评之间最大的差异表现在对待真理的态度上。教条批评家以真理的占有者自居,把依照他们的某一教条得出的作品的意义强加给读者;而内在论批评家则放弃对真理的探索、放弃价值判断,只对作品进行客观描述。很显然,这两种批评都不是对话式的,因此也无法实现批评家与作家共同进行“真理的探索”。蒂博代在论述自发的批评时,说:“一位这样的批评家应该满腔热情地拥抱当代的作品,努力与作者建立起心灵的通路,而不是用现在的标准去衡量长短,曰某是,曰某非,·俨然手中握有通往后世的通信证。”他还说:“现在有些性急的批评家热衷于裁判是非,评定优劣,恨不得天下的作家都像他希望的那样子写作。”蒂博代的话好像就是在批评当前文艺批评界某些人。在各种作品研讨会上,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对作家指手画脚的批评家,好像他们是文坛的“太上皇”,好像他们掌握着作家、艺术家的生死命运。尤其有些批评家以为文艺创作就应该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来发展,他们没有把自己当做作家、艺术家的平等的对话者,而是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作家和艺术家。
当然,文艺批评不排除价值判断,不排除批评家的主观意见,甚至不排除批评家严厉的指责,因此在批评时发出不同的、甚至对立的声音也是正常的,但不同的声音恰恰是对话的前提,而且批评家与作家、艺术家共同探索真理时,他们之间就不会存在根本的分歧了。如果某一位批评家自以为掌握着文艺的生杀大权,完全决定着当代作家和艺术家的命运,那他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事实证明,很多作家即使从来没有批评家的意见来支配,照样能够创作文艺作品,而且批评家虽然在促进文艺作品的传播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他们的批评在作家、艺术家进人文学史视野的过程中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甚至有些身处作家协会的主流批评家还控制着文艺评奖,有些学院批评家还控制着文学史、艺术史和文学作品选读等教材的编写,但这并不能否认批评家与作家、艺术家之间平等对话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不过,对话的批评也要求作家、艺术家有真诚的人格,有自我反省的勇气,有倾听批评家声音的姿态。如果作家、艺术家自以为是、霸气十足,那么,对话的批评也就很难展开,而批评家的良好的交流意愿和负责任的批评行为就很难得到有效的回应。
蒂博代说:“文学正常状态得以建立,几乎一边是作家,一边是有道德的、有修养的、有耐心的读者”。创作和批评是文艺景观的两个方面,良好的文艺生态既需要有创造力的作家、艺术家,也需要有胆识、有才情、有操守的批评家。当前文艺创作总体上是相当繁荣的,不但文学出版繁荣,比如长篇小说每年的出版量就超过了1000部,儿童文学图书也占据着大量的市场份额,至于影视和动漫艺术等,更是越来越拥有巨大的消费市场。而且新的文艺样式和新的表达方式不断涌现,急需文艺批评发出自己的有效且有力的阐释与批评的声音,可以说,文艺的新时代呼唤有公信力的和有艺术渗透力的批评家。
二、调整文学批评的视角
电子媒介出现以后,文学创作发生了分化,作家之间的代际冲突也越来越大。但仔细观察会发现,当前的文学批评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缺乏系统整体的观念和开阔的视野,没有把文学发展放到大文化环境中去考察。对具体作品,尤其是对长篇小说作品的商业化推广做得多,对优秀作品的挖掘与解读不够,而且批评的对象还显得狭小,社会影响力不够,没有发出应有的声音。事实上,今天的文学已经面临产业化的问题,而且文学生产、传播与接受已经被纳入到了产业化的机制之中,文学理论批评是不能绕过产业化这道坎的’有效的批评必须从文化产业结构分析的角度来分析文学的生态,来看待文学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