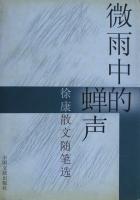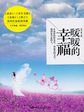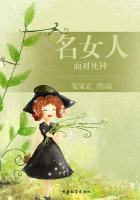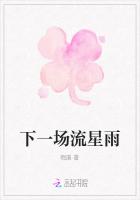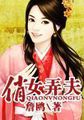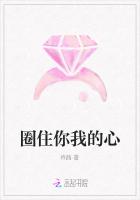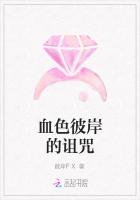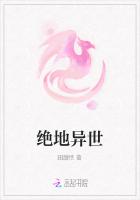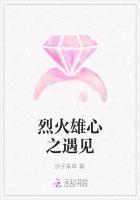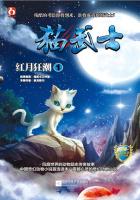那天学校大操场上鸦雀无声,气氛很严肃,空气很沉闷,大家都专心地听着刚来不久、面孔阴险、嘴上不时叼着香烟的刘校长(兼党委书记)数落王主任犯下的“十大罪状”。这十大罪状主要是跟阶级、阶级斗争有关。具体哪十条记不清了,但使我刻骨铭心的一条是:
竭力将黑帮子女塞入大学,把“革干”、工农子弟排斥在大学门外。
更使我惊讶无比的是,他列举的“黑帮”子女竟然是正寄住在我们家里的同乡兄长黄显亚。黄显亚的父亲跟我父亲是四川富顺县老乡,他们家在成都暂时没有住房,我爸就让他们全家搬到我家来住,大家相处得和睦、亲密。黄家是四兄弟,黄显亚行二,比我大一岁,高我一个年级。他很聪明,读书读得很轻松,学习成绩非常优秀。他父亲是个知识文化水平相当高的人,却没有在大单位上班,而是在一家搬运队拉板车,干重体力活。这次才知道他父亲解放前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又是什么“袍哥”组织的小头头。
大会上的发言人声色俱厉地批判王主任故意不执行我们党的阶级路线,竟敢为黑帮子女黄显亚的高考开绿灯,为其升学保驾护航,强行塞入北京某重点大学,而把某某干部子女排斥在大学门外。
此后,成都市招生办确实传出一段精彩的故事:1964年高考没有公布考生成绩。黄显亚的高考成绩非常好,经查实,他各科成绩都在85分以上,是成都市理科第一名。他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第二志愿是北师大,第三志愿是北京钢铁学院。录取过程中,清华、北师大的招生工作人员犹豫很久,不敢要。北钢的招生工作人员得到后就不肯放手。
他们说:这么好的学生哪里找?他们不要我们要。北京钢铁学院决定立即录取,当天下午就把录取通知书交给了邮电局。第二天一早,市招办主任接到市教育局某领导打来电话,要求马上扣压这份录取通知书。市招办主任放下电话就往邮电局跑,到邮电局一找,晚了一步,说邮递员刚带走。市招办主任决定尽最后的努力追。他先打电话问好黄家地址,再请邮局派人快速赶到黄的家门口去拦截。结果不妙,派去的人赶到黄家时,刚好遇见送通知书的邮递员走出门来。木已成舟,无可奈何。(听说,黄显亚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在北钢学习不到两年就把专业课自修完,学院图书馆的相关书都翻了一遍,第三年考上本校研究生。)其实,这事并不是王主任要把黑帮子女黄显亚塞入大学,而是因为北京钢铁学院的招生人员还有几分良知和勇气,根据考生家庭和成绩自主地择优录取而已。从批判会不难看出:为了在后来的招生推荐工作中切实贯彻落实阶级路线,学校当局要抓一个典型,搞杀鸡儆猴的勾当。
这件事情给我的打击很大,使我对升大学的想法产生了绝望。论成绩,我不及黄显亚;论家庭出身之差,有过之而无不及(前已述及:我的家庭出身里面比黄多了一个“叛徒”性质和“关管杀”成分)。姑且算我成绩过关,那个严格的政审关就难过了,新上任的教导主任绝对不敢步王主任的后尘!我已清楚地意识到,摆在我面前的1965年高考将有一个令人心寒的结果(那一年毕业的考生档案里都附上了学校推荐意见。据我们年级二班田毅生同学说,他的学生档案被“文革”造反派抄出来,上面学校推荐意见栏写的是“该生不宜上大学”。他没有想到断送他大学梦的竟然是自己的班主任和母校)。
我该怎么办?1965年最后下半学期都没有专心读书,而陷入了深沉的思考、激烈的斗争和痛苦的抉择之中,一味要升大学的想法开始向上山下乡转变。
对每一届高中毕业生,学校都要作“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宣传教育,对我们这届学生作的是“一颗红心,多种准备”宣传教育。也就是说,除了升学与就业两种准备,我们还需要有待业、无业等多种准备。在阶级斗争路线指导下,出身“黑五类”的学生就有必要作好这些准备(事实上,六四、六五两届出身不好的学生待业而街道办事处不予分工作的太多了)。其实我在想,就算我走运,没升到学而让我就了业,高中毕业当徒工去卖体力,我还真不愿意干;况且最关键的问题是背上背着出身不好的皮,随便在哪里就业都一样受歧视,何时出得了头?“文革”期间广为流传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等反动血统论更使出身不好的人抬不起头。人活着就这样低着头,夹着尾巴过日子有什么意思?我想,我们还这么年轻,总不能因出身不好而沉沦下去吧。要想办法,要思变!那么,想什么办法,怎么变呢?辗转反侧地想完了,最后结论只一个:“脱胎换骨”吧!
“脱胎换骨”意味着出身不好的学生能真正背叛家庭,能真正与父辈的反动思想、言行划清界限,做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当时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家庭出身重在看本人表现。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要争取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脱胎换骨”意味着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吃得苦中苦,方为接班人;意味着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意味着到艰苦的地方去,“真金更要火来炼”!
最艰苦的地方在哪里?在边疆,在贫困的山村,在无人愿去的穷地方!
那两年,“有志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等等之类的标语、口号比比皆是。几乎所有报纸杂志都大幅刊登某某知识青年放弃城市的舒适生活,主动上山下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事迹。全国着名的知青有邢燕子、董加耕;四川着名的知青有巫方安、孙传其;成都也有,名叫张宏道。张宏道曾被请到我校给我们作过一次报告,讲述了他如何毅然决然地回到家乡-凤凰山,如何把一个荒山变成花果山,如何从一个不起眼的果农变成一个远近闻名的园艺师,如何从普通劳动者提拔为乡镇领导。回乡知青董加耕有一句话:
“吃得苦中苦,方为接班人”。确实,坚决要求到艰苦贫寒大凉山插队落户的成都市十一中学高中毕业生巫方安、孙传其,不到一年就分别被推选为当地人大代表,入了党,还都身兼当地政府要职,政治地位高了,名气也大了。而她们原家庭出身并不怎么好。
我想,他们能选择这样的道路,我就不敢吗?我怕啥?不就是“用青春赌明天”嘛!
那时真有点“宁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气度。干脆来个“不成功则成仁”的做法又如何?这个想法给几个相好一交流,立即产生共鸣。暗中串联后,我们高三四个班共十来个人联名向成都市团委发去一封“请允许不参加高考,坚决要求到大巴山革命老区插队落户”的申请报告。(这十来人中有大半是出身不好的,他们很认真,出身好的人不多,大多是闹着玩的,他们中最后有一个是真下了乡)团市委对我们上山下乡的决心非常支持,但要求我们必须参加高考。最后除袁学鑫同学外都去参加了考试,袁学鑫一直在考场外给大家守包包,无论怎么劝他都坚决不考试。为表示决心,三班的任伦同学从写申请那天开始,天天打光脚,一直坚持到下了乡都未穿过鞋。
我也动了真格。成都有个编号叫“102”信箱的国防工厂(现在的西南金属结构厂)给我送来当工人的招工录取通知书,被我毅然拒绝。我父母和好友亲临成都上山下乡知青训练班苦口婆心地劝我,我没动摇,而是把招工录取通知书上交给了知青训练班领导。
因此我的下乡决心引起轰动,受到当局嘉奖,在获奖学员中排名第一。就这样我坚定不移地走上了上山下乡这条能使人“脱胎换骨”的艰苦道路。我们成都九中最后一起踏上这条人生艰苦历程的高中六五级同学共20人,初中六五级同学共三人。其中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现在看来真是又可笑又可悲。下乡五年,我既没有脱什么胎也没有换什么骨,只是徒然消磨了青春岁月!
作者简介
张学锜,男,汉族,1946年8月生。1965年成都九中(现为成都树德中学)高中应届毕业生,1966年3月到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县高草人民公社插队落户。1971年12月调回成都市食品公司搞兽医卫生检验。1977年至1981年在成都大学学习,毕业后在成都市食品公司职工学校任教师、副校长、校长。1987年调省乡镇企业管理局企业指导处任质量管理工程师。1992年调四川省乡镇企业培训中心主持全面工作,任副主任、主任、书记。2003年至今在四川凌峰矿业公司任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为了那些被湮没了的岁月
韩秀
什么事情都有着一些缘由,说到上山下乡,就不能不说到更早些的故事。想想也真是感慨得很,从1982年开始写作,在台湾和美国已经出了将近三十本书,写到作者简介时,长长的这一段故事总是被省略掉了,生活在台湾的人们不懂得“上山下乡”这个词儿是个什么意思。当然,那只是一方面的原因。结果就是,这些被湮没了的岁月竟然被深深地藏进了心底。
我的父亲是一位美国的军人,他在1943年到1945年这一段时间里,担任美国驻华使馆的陆军武官。那时候国民政府设立在陪都重庆,美国大使馆自然也设在重庆。父亲在重庆住了两年,在盟军丢失了缅甸、滇缅公路被日本人切断、中国人民“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他担任的工作是保证美国的援华战略物资的“驼峰”运输、协助中国政府装备和训练中国远征军、重新打开滇缅公路、从日本人手里夺回东南亚。所以,说到底儿,我的父亲在中国期间所做的事情是真正地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父亲在重庆也认识了我的母亲。1945年,日本投降,“二战”结束,我的父亲带着我的母亲离开了中国,返回美国纽约。1946年,我出生在曼哈顿。当时父亲正驻节新西兰,他赶回曼哈顿,看到了我,然后返回工作岗位。
这样的一段故事,自然不能见容于1949年之后的新政权,因为中美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一直是敌对而紧张的,而父亲不但是军人,且与1949年之前的国民政府合作很密切。在新政权眼睛里,他无疑是“敌人”。于是自从“抗战”胜利离开中国,父亲再没有机会踏上中国的土地。
我却在一岁半的时候被我母亲托付给一对美国青年,他们带我搭乘一艘美国军舰,漂洋过海来到了政权更替中的中国。在上海接船的,是我的外祖母和她一位远亲赵清阁女士。直到1978年我重回美国之后才知道,我是在父亲不知情的情形下被送走的。当父亲听说他唯一的女儿被送走的消息赶回华盛顿的时候,我已经抵达上海了。父亲1968年过世,在我的一生中,我与他竟然只有出生时的那一面之缘,那是深深的无法言传的伤痛,永远无法愈合。
我是跟着外婆长大的。外婆是无锡人,出身富裕的大家庭。1937年外公去世后,外婆便考进国民政府的统计部作了一位公务员。政权易帜,外婆为了等我而失去了南迁的机会。她深深了解,如若住在南京,恐怕很不安全,所以索性来到北京,在米市大街一个小三合院安安静静地住了下来。我婴儿时期的乳娘是一位日本妇人,所以我开口学话便是日文。在船上与那对善良的美国夫妇在一起,只有英文,丢掉了日文。与外婆在一起,学了一口无锡话,又丢了英文。到了北京,学了一口纯正的北京话,虽然听得懂无锡话、上海话,却说不利落了。后来,住过无数地方,学习过各种不同的语言,北京话却跟了我一辈子,无论如何,难舍难分。
外婆是一位极聪慧的女子,她深深知道她是我唯一的依靠,保护好她自己就是保护了我。所以,她留在了家里,靠修缮书籍谋生。那时候,许多人仓皇离去,许多的珍本书流落街头,中国书店用麻袋送来残卷,外婆将它们整理成一套套的线装书。做这件事首先需要懂得断句,然后需要修补书籍的工具与技巧。现在正流行德国作家冯克的一部书,叫做《墨水心》,里面有一位书籍装帧师莫提玛,每当我读到他把一卷修书工具打开的时候,就会想到外婆那一套工具:在一个缝得结结实实的青布卷囊里,除了大小不一的各式刀剪之外,还有许多厚薄不一的竹片,它们被磨得温润无比。外婆告诉我,她从小就跟着她母亲修补旧书,那是一项传了若干代的技艺,可以追溯到上百年前。她手里的这套工具还是她出嫁的时候外曾祖母给她压在箱底的呢。于是,从外婆那里我学到了“艺不压身”这样一条人生路途当中应当谨记的道理。我还记得那一架木头做成的订书机,外婆坐在凳子上,订书机哐当哐当地响着,线绳整齐地穿过修补好了的书页,将它们装订成板板正正的书册。
其中的一些书在交还给中国书店之前,成了我的启蒙课本。我四岁发蒙,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些书将我引进了传统中国文化的大门。讲句老实话,对我来讲,中国古典的文学、哲学实在是一种最为坚强的精神支柱。它们在我最没有指望的日子里让我守住了内心深处的那一块净土,真正非同小可。近些年来,东西写得稍微多些,有人说,这人长了一张西方人的脸,行起事来却是地道的中国人,而且不是现代的中国人,而是古代的中国人。我想,他们之所以一语中的,无非是看到了感觉到了中国古典文化对我的深刻影响。每到这种时候,我都会深深感激外婆当年的睿智。
外婆没有进入任何一个“单位”,1949年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也都没有波及到她。外婆娘家和婆家的亲戚们在土改当中都被整肃得七零八落,她却早早就离开无锡的大家族了,靠薪水吃饭,成分便被划为“小土地出租者”,不算太“高”。如此这般,一直到“文革”
之前,她都可以生活得比较平静。
少年时还有一些际遇也很有意思。前面谈到的赵清阁女士是外婆的远亲,我唤她“清阁姨”。因为她在戏剧与小说方面有一些成就,文化圈里的人们都尊称她为“先生”。
赵清阁女士与老舍先生是青年时代的合作者,知情的人们说,舒庆春写剧本完全是赵清阁推动的结果。我不可能知道得那么深远,我只知道,清阁姨一生未嫁,单身住在上海,而老舍先生与妻子儿女一大家子人住在北京。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搬到了干面胡同,我就读的学校在灯市口,从灯市西口到乃兹府舒先生家就很近了,我常常穿梭在这一带。清阁姨寄信到外婆家,我便将信揣在怀里,来到舒家。大清早起,舒先生正浇花儿,我就把那封信悄悄儿地从花叶子底下递过去了。
舒先生的回信也如是,我带回家,由外婆再寄到上海去。这样一种忧伤而温柔的柏拉图式的精神交流,深深地感动着我。现在两位老人家都到了一个可以尽情聊天的地方去了,每想到他们,我总是很高兴,因为我曾经成功地为他们传递了他们迫切需要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