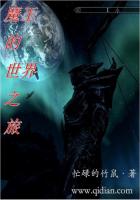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为一名曾经留学日本而又着作丰硕的作家,郁达夫作品中那种独特、鲜明的个性色彩以及由此渗透、显示出的非凡的才情学识早已为人们所公认。但是,翻阅他的日记、散文和游记,人们又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学识渊博的作家,竟然会对求签问卜、看相算命等迷信活动颇感兴趣。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几乎每个阶段,每到一处,他都要抽个签,占个卜,仅在他的日记、散文和游记中,有具体文字记载的这类活动就不下十次。
1921年10月,郁达夫首次去安庆安徽法政专门学校任教,刚到安庆没几天,他便在与几位同事去菱湖公园散步时,特上吕祖阁求签,结果得到的是一张与他当时的心境颇为相近的九十四签下下:
短垣凋敝不关风,吹落残花满地红。
自去自来孤燕子,依依如失主人公。
1926年12月,他乘船离开广州赴上海主持创造社出版部的事务,途经福建马尾时遇风受阻,于是他特去参谒了位于马尾罗星塔畔的马水忠烈王庙,并求签得第二十七签:
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山明水秀,海晏河清。
这天恰好是冬至,庙中的管长,正在开筵祝贺,见这大吉大利的签诗,向他祝贺称道了一番。
1927年春夏之际,郁达夫与王映霞正双双坠入爱河。这年的4月和6月,他们先后两次去杭州时,也都乘在西湖游玩之机,去位于漪园的白云庵月下老人处求签,卜问他们这一场恋爱的前程。据郁达夫在日记中说,两次抽签的结果,都预示着他们的这一场恋爱大约可以成功。其中6月23日求得的五十五签云:
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圆聚,愿天下有情的多成了眷属。
移家杭州后,他在建造风雨茅庐时,又特地请杭州闻名的风水先生郭相经多次前来指点,诸如大门的方位、正屋的坐落、门窗的开辟、日期的选择,甚至连原先设想的五间平房改为前三后三两进的整体设计,都一一按照郭某的建议定夺。郁达夫曾在《记风雨茅庐》一文中,对这位风水先生大加推崇,说他是一位具有通天入地眼的奇迹创造者,同时也是读过ABCD,学过代数几何,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学校毕业生。其实,这位郭某仅是杭州一所旧制中学的毕业生,根本没有受过什么高等教育,只不过凭借着一套江湖术士的本领,便花言巧语地将郁达夫说得头晕目眩、天花乱坠。
奇怪的是,这位江湖术士也竟然准确地说中了一件事,他曾对郁达夫和王映霞说:
“这所房子落成后,除出人口平安,家运兴隆外,屋主人立刻可以得差使。”
果不其然,房子还没有竣工,郁达夫便收到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招募他南下任职的信。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一点,郁达夫才对他深信不疑,大加颂扬。
南下福州后,郁达夫仍不时求签问卜,他在1936年4月7日写的日记中,就曾具体地记载了这天他去福州白塔下瞎子陈玉观处占卦算命的详细内容:
……陈谓今年正二月不佳,过三月后渐入佳境;八月十三过后,交入甲运,天罡三明,大有可为,当遇远来贵人。以后丁丑年更佳,辰运五年——四十六至五十一——亦极妙,辰子申合局,一层更上,名利兼收。乙运尚不恶,至五十六而运尽,可退休矣,寿断七十岁(前由铁板数推断,亦谓死期在七十岁夏至后的丑午日)。子三四,中有一贵。大抵推排八字者,语多如此,姑妄听之,亦聊以解闷而已。
自此以后,他每到一处,仍旧喜欢求签占卜,这在他后来写的一些散文或游记中也有记载。
令人不解的是,孙百刚在《郁达夫外传》一书中详细叙述的一次他的一位表叔给郁达夫看相的事,无论在郁达夫的日记、文章还是王映霞的回忆、自传中都只字不提,没有透露出一点消息。
据孙百刚在《郁达夫外传》一书中说,那是1937年春,一次郁达夫从福州回杭,和王映霞一同去孙家拜访。闲谈之中,孙百刚无意间提到他的一位在杭州某银行工作的表叔朱似愚,也十分精通堪舆命相之术,只不过平常不肯轻易替人谈相看地。郁达夫一听非常动心,一定要他将表叔约来谈谈。
于是,孙百刚就决定星期日请郁达夫、王映霞和他的那位表叔一起来他家吃午饭。
到了星期日,别无他人,就是朱似愚和达夫、映霞来家中便饭。似愚先到,我就将达夫要请他谈谈命相的意思告诉他。他一向不愿意亲友替他宣扬,经我说明达夫是我多年至好,不比寻常泛泛之交,同时,他也知道达夫大名,当然只好答应了。那天,达夫和映霞来得很迟,一到,大家先吃饭。
饭后,似愚请达夫朝窗口坐定,他仔细向达夫端详了一番,一声不响,只是一口一口地抽烟。我看似愚神气,似乎非常为难。这时达夫果然正襟危坐,一心不乱地等他开口。就是在旁边的映霞、纪瑞和我,也都屏声息气望着他。
“郁先生今年贵庚?”好不容易逼出了似愚一句话。
“我是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年生的。”
“郁先生晓得自己的四柱吗?”似愚问他的八字。
“是丙申,庚子,甲午,甲子。”达夫很内行地背了出来。
“目下交什么运?”似愚沉思了一下。
他知道达夫是熟悉自己的八字的。
“记得交的是甲木运。是四十一岁交进的,甲运下面是辰运。”达夫告诉了似愚。我很诧异达夫何以如此内行。
“嗯!”似愚听了达夫的话,表情不好,仅仅鼻中哼了一口气,又抽起香烟来了。过了两、三分钟才开始说:
“以前的事,我想不用多说。你先生在甲运以前,一直都还不错,不过也是镜花水月,虚而不实。以后的运却要相当注意。三五年内,波折不少。假使能自己生场大病,或者家人有点疾病,那算是幸运了。但命相之说并非一成不变。修心可以补相,居易足以俟命。你先生是通达之人,用不着多说。总之,今后数年中,凡事小心在意,能不出门最好莫远行,能忍耐受气,切莫发火暴躁。你和我这位表侄是多年至好,所以我也不揣冒昧,交浅言重了。”
似愚说了这么一段,其间还有很多命相上的术语,我也记不清楚,只知大意如此而已。
人总是喜欢听好话的,即使明知道好话是假的。本来预定映霞也要请他谈一谈,听他如此说法,映霞的胃口也倒了。
他们夫妻谈了不多一刻,告辞回去。等他们走后,我和纪瑞追问这位老表叔,到底达夫的命相,坏到如何地步,何以要如此说他,使他乘兴而来,败兴而返。
似愚不慌不忙说了一大段,大意是:
“我哪敢当面对他直言,只不过略略讽示一二而已。老实说,要我完全违背了相法命理,作违心之论,阿谀之言,那是不可以的。其实这位郁先生的命相,我也阅人不少,今天可算是一桩巧事。总而言之,他的命相刚到目下为止。从今以后或许要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倘若自己性命能够逃出,那是祖宗的阴德了。”
“竟凶到如此地步吗?他目前新造洋房,新得差使,似乎好运刚开始呢!”我表示怀疑。
“差使,洋房,无非是身外之物,就是妻子儿女,有时也保不定的。”他用看破红尘的口气说。
“莫非不可避免吗?”我总觉不信。
“那也不能这样肯定。我不过就相论相,就命谈命而已。”
他没有再说什么。
我知道这位老表叔的脾气,也就不多说了。
听了表叔的这番话,孙百刚不禁毛骨悚然,大为惊骇。
可是,将杭州朱似愚的这番扑朔迷离而又似乎言之凿凿的预言与福州的那位瞎子陈玉观所说的“渐入佳境”“名利兼收”“当遇远来贵人”“寿断七十岁”的种种推测相对比,便清楚地表明,这些截然不同的“先知先觉”也正说明了占卦算命的虚妄荒唐、不足为凭。难道朱似愚的这番故作高深的警示就一定比盲人陈玉观的胡言“瞎”说准确和高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