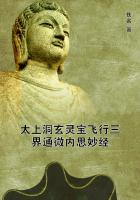从那晚以后,沈曼辞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举动,只是不分昼夜地睡觉,晚上总是睡了又醒,反复做梦。
但是为了防止突然发生什么意外,林舒卿每晚都要守到很晚才睡。沈曼辞一直不开口,林舒卿也不问,她想如果她愿意说,迟早也会告诉她。
沈曼辞在凌晨醒过来,这几天她过得浑浑噩噩的,现在觉得精神好了一点。她小心翼翼地起床,去厨房给自己倒了杯水。
挂钟上的时针指在四和五之间。
初冬的白昼时间短,这座城市还笼罩在微蓝的天空之下,窗台上的瑞香浓绿黄白相间,它的花期快要到了。
一早接到封如深的电话,这几天他都在处理封家的事情,所以一直都没联系到她人。
赶到医院的时候,病房外聚集着不少的人,气氛很是压抑。沈曼辞预感到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
封如深的脸色阴沉,身边有不断的人在他身边来来去去,封如深看到她来,把剩下的事交给封文宗处理,快步走向她。
几天不见,她似乎一下子消瘦了很多,眉眼间都有挥之不去的疲惫。
“叔叔的情况怎么样了?”
他看了病房里一眼,嘴角呈一条直线。
“早上下了一张病危通知书,能不能熬过去就看今晚了。”
沈曼辞大惊,平身第一次离死亡如此接近。
她不知道此刻自己该说些什么,其实说什么也是徒劳。眼前的男人,碧蓝色的瞳孔失去了耀眼的光华,尖削的下巴上不满青色的胡渣,让人心焦。
“生死有命,相信叔叔看到你现在这样一定也心疼的。”
封如深笑了笑,揽着她坐下,把头靠在她的肩膀上小憩。见此情形,外人都知趣的离开。沈曼辞渐渐地也闭上眼睛,忽然觉得时光正缓慢的穿流在他们之间,一点点消失。
下午的时候接到吴敏慧的电话,说今天她的报告就可以出来了。其实不用她告诉结果,她自己心里有数。
她没有回家,而是坐上出租车返回医院。她看着上面写的确诊结果,心里却突然释然了。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放电影般在她脑海里闪过,她忽然想念起凯瑟琳和珍妮弗。
沈曼辞出去一整天,林舒卿也没有任何举动,第二天起床的时候,沈曼辞已经把早饭买回来了,她看上去很精神,和前几天的神态大不一样。
她倒是觉得沈曼辞之前的困顿远比现在这样强忍着要正常很多,她现在故作安然自若的样子让她气滞。
“昨天你去哪了?”
沈曼辞的愣了一下,随即端起碗吸了一口粥。
“去了趟医院,认识的一个朋友的爸爸生病快不行了,我去陪陪他。”
气氛突然安静下来,只听见吃东西发出的砸吧砸吧的声音。
“曼辞,跟我回去吧。”
“嗯,会回去的。”
林舒卿猛地掷下筷子,这近半年的时间发生了什么孟予箫都和她说了一清二楚。她最恨的就是她受尽了委屈,吃够了苦头却仍是执迷不悟。
“那是什么时候?”
她开始气势逼人起来。
沈曼辞回国之前,她就不对沈曼辞的想法抱多大的希望,如今事情演变成这样,她更加坚定了要带她回去的想法。
“还有一些事情没处理,处理好了就回去,可以吗?”
“还有什么事?你说要找你亲身母亲,结果找到了吗?你说你遇到了小时候绑架你的人,你喜欢他,那他对你呢?沈曼辞,你活的累不累?别人的事统统和你有份,圣母玛利亚都没有你慈悲!”
她的一席话触动了沈曼辞心底那根弦。她说的都是事实,证明她是个执迷不悟的傻子。她放下碗筷看着她。
“我想要的是,受了什么苦受了什么累,至少有你在,我也不怕了,而你现在只是在挖苦我,让我认清我自己。”
她们两个人的脾气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倔强,不懂得让步和盲目执着。认定心中的念头就不会轻易改变。
“我难道不都是为了你好吗?其实你早就把找你母亲当做借口,都是为了那个不可能的男人所以才那么苦苦挣扎,以为不告诉我我就不知道了吗?我心疼你,恨不得打你一顿!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我有多难过!”
林舒卿几乎是吼着说出这些话,沈曼辞看到她的眼睛充盈着泪水,忽然心里一软,鼻头泛酸。
“我知道你们都是为我好,可是你们不知道我是最难过的,我以为我找到我妈妈了,可是我错了,我以为我能让我爱的人爱上我,可是我却因为他一次次伤害我自己……”
她的眼泪溢出,回国以来的所有委屈她都想声嘶力竭地发泄出来。
“我也恨不得打自己一巴掌,我怎么这么傻,这么贱,每次我一个人痛哭的时候我都告诉自己,不要再喜欢他了,他不值得的,可是第二天我又忘记了……”
她捂住自己的脸痛哭,眼泪像是不断地从他的指缝落下来。
残酷的现实,绝望的处境和美好期许的破没都将她逼得奔溃。林舒卿走过去把她的头按在自己肩头,不停地顺着她的脊背。
“你不要自己硬扛了,跟我回去吧……我说过我一直在的,我好好照顾你……我们一直一直在一起。”
两个人相拥而泣,对话持续到傍晚余晖满天,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她包里的确诊书露出边角,林舒卿抽出来看,而后只是更紧地抱住她。
就让这个成为她结束痛苦生活的借口吧。
经历过前几次的风波,孟氏又恢复了原本的秩序。大家平时的谈资也变成了傅何时或者孟予箫谁今天穿了什么衣服,对谁说了什么话,不过话题人物从不会出现孟良鸠和沈曼辞。
刘梦瑶已经被辞退,理由是私自篡改公司重要文件,傅何时特地派了一个小组专门彻查这件事,即使真相大白后,无辜受害的沈曼辞却也再未在公司出现。
“新港街的拆迁工程已经全部完成,近期就可以动工,预算超出百分之三,财务部准备拨款……”
钟秋心有条不紊地给孟良鸠读着关于工程的进展和事项。孟良鸠单手支着额头,整个人靠在椅子上,眼神似乎定定地看着什么。
等到她念完,他还是保持着这个样子。钟秋心知道他根本没听进去。正想开口提醒,他却突然让她先出去。
她转身走出去几步,又折回来。
“老爷子那边派人过来招呼过,万一封家真有什么事,要我们不遗余力地帮忙。不过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趟这趟浑水,封如深这些年来任性妄为,没少惹到别人,现在封秦天不行了,那些人一定会趁火打劫,这样反倒会牵连我们。”
孟良鸠不说话,打开电脑自顾自干起自己的事情,钟秋心的眼神逐渐黯然。
寒假快来了,沈曼辞决定在学期期末向学校提交结束交流生的课业的申请书。
深冬的时候,瑞香花也完全败了。沈曼辞接到封如深的电话,封秦天去世,拖了这么些天,他到底还是没能挨过去。
她匆匆地赶到殡仪馆,灵堂上正中央摆放着封秦天的遗像,周围都是别人送来的花圈。封如深一袭黑衣,衬得他苍白的皮肤愈发病态,他低垂着头,向前来吊丧的人行礼。
沈曼辞从后面绕到他身边,轻轻握了握他的手,封如深看向她,眼里尽是凄惘。
孟家和封家是世交,如今封秦天去世,孟老爷子自然是要带着家人来的。
傅何时一眼就看到了和封家人并排而站的沈曼辞,已经有很久没看到她,现在却在这见面,他难免惊讶不已。
“曼辞居然也在这。”
闻言,孟良鸠循着看过去,看到那抹纤弱的身影,敛了敛眉,深邃如海的眼眸泛起细微的波澜。
老爷子和封家人一一握手,说了些宽慰的话。走到封如深面前,他抬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如深啊,你父亲去世,封家就交给你,你担子就重了,如果有什么困难尽管找我,你爷爷当年对我有恩,我一直记着。”
老爷子语重心长地说着,封如深不答,只一味恭谦地点头。
沈曼辞一直微低着头,下意识地不想看到他们一行人。她刻意回避的行为让他眉宇间无端添上几分不悦。
临走的时候,孟良鸠经过她身边,沈曼辞感到一股压迫感,她看到他细白的手腕上那隐约的一圈疤痕一飘而过,心中泛起一层涟漪,又很快消失。
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沈曼辞是外人,也不好多待,免得别人说闲话。
走出殡仪馆,孟良鸠靠在他那辆阿斯顿·马丁上抽烟,他英俊的面容在余晖的之下温煦清寡,薄唇轻吐氤氲的白烟,身影有些孤寂。
他抽烟的时候总有几分颓唐的凄迷味道,只有经历过太多沧桑的人抽烟的模样才会有这样好看。
沈曼辞心知他一定是在等她,她有很强的预感,于是心里也释然了,迈着步子向他走过去。
孟良鸠掐着烟看她,她也看着他。有人说人的眼睛会泄露他的一切,可是沈曼辞什么也看不到。
“你还要休多久的假?”
他的话不免让她生出既可笑又失落的情绪。
自从上次酒会之后,沈曼辞再也没去过公司,傅何时和钟秋心都给她打过电话,可她一个也没接。她还有什么脸面再回去若无其事的工作?
“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我在想,你是还想继续看我狼狈的样子,还是舍不下我不在你身边?”
他又抽了一口,然后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辗灭。
“你觉得呢?你觉得,会是哪一种?”
他语气里的颓唐使沈曼辞忽然有些恍惚,他一向是对人恶语相向,更是不遗余力地打击她,她也准备拿出强硬的态度,这下却手足无措起来。
沈曼辞知道他从来不是在自己预想范围之内的人,把握不住,所以对待他总是诚惶诚恐。
“狠狠打我一巴掌,现在又问我枣要不要吃?孟良鸠,我太不懂你了。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不追着你心理感觉很不平衡吗?”
她咄咄逼人的模样完全和平时的沉静温婉大相径庭,孟良鸠心里一窒,忍不住出手地圈住她的腰把她带进怀里,水光潋滟的眸子慵懒地睥睨着她,带着不耐和强硬。
“你不是要我爱你吗?爱不是你一个人的事,要我爱你,还得看我愿不愿意给。”
沈曼辞不明白他这些话的意图,也不想再去多费脑筋。她挣扎了这么久,区区混沌的几天让她想明白,她还是得像当年那样离开,这里没有东西她能带走或是得到。